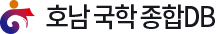- 국역/표점
- 표점
- 대곡유고(大谷遺稿)
- 卷之五
- 雜著
- 知舊問答
대곡유고(大谷遺稿) / 卷之五 / 雜著
知舊問答
厚允曰。性也者。乃兼氣而言也者。始看甚駭然。及看下段以性之所以得名之實而言然後。乃知其言意之所在。非若以性爲和泥帶水看者也。盖理之在物。名之曰性。果以其生之理具於心。故其爲字從心從生。先儒之釋字。義甚精密。無可疑。而景範之爲是言也以此。先生之云答說是者。亦以此。然語病終覺有之。性之在物。譬如人之乘馬。水之儲盤。而稱人稱水。皆單指人而謂人。未嘗兼馬而稱人。單指水而謂水。未嘗兼盤而稱水。此性卽理也之說也。此程子之有功於聖門。而朱先生之一生頭戴者也。今曰。性也者。乃兼氣而言也。則是幷人馬而稱人。混水監而稱水。不亦有病乎。見處之病。固是重症也。下語之病。亦不可謂無恙也。盍以此更質於先生耶。近世韓南塘言。性卽在氣之理也。南塘於程子本語。添在氣之三字者。盖以性謂因氣而得名而然也。夫理不在物。則不名爲性。其以性爲因氣而得名。其言性謂在氣之理者。皆未爲不可。而一有此知見。轉轉醜差。以仁義禮智。亦欲兼氣而言。遂以太極之本然。爲懸空底物事。此非可戒耶。且曰在氣。曰因氣。則歸重猶在於理也。曰兼氣。則是性也半理半氣。孰重孰輕。兼字字義。逈別於因在字也。然則語病非特爲南塘而已。雖然南塘見處之病也。景範下語之病。固不可比而同之。而後生之隨語生解者。若執据兼也一句。則幾何而不爲南塘也。或人有皮膚小痾。良醫者診之曰。脈不病。是何足爲病。或人遂不以爲病。爬痒致毒。終成大腫。盖景範之語病。皮膚小痾也。先生之是之者。以脈不病也。願景範勿以先生之是之。而不復致思也。合虛與氣有性之名。此正周子所謂五行之生也。各一其性之意也。各一其性。非太極之本然耶。則以其不離乎氣。而槩以兼字命名之。可乎。墮在氣質中之說。朱子答徐子融書也。徐盖外本然。而別求氣質之性。以本然氣質。分作兩性看。故朱子以本然氣質之合一者言。以明本然之性。不離乎氣質。氣質之性之不外乎本然也。是以其言如此。意各有在也。明道人生以靜一段。意亦如此。引此以證性之不離氣質。則可以證性乃兼氣也之說。則恐或過矣。答曰。性乃兼氣而言。此一句使渠自觀。猶不勝駭甚。雖曰語病。實是知見未到。若使執言而不問旨。則去荀揚。在毫髮頃刻間。此是吾家頭腦命脈在處。一差則餘無可論。而不知不覺。此身坐在裏許。誠甚慨然。吾兄可謂濟人於九淵之中矣。何幸何幸。來喩明白精密。
不侍更稟。而已無所疑。
厚允曰。先生答問中。理之有善惡。因氣而有云云。此段問答。可謂極窮到底。發前賢所未發者。求之於心。察之於行。造次顚沛。母敢有所差失於所謂中者。則大本斯立。逹道斯行。此非吾輩家計耶。但說理不如說中。中則無不盡也。此二句。使不知者看之。或不能無疑。疑於低視理字裏面。有若包不善自在者然。此則先生於答人問第三段。已明言之。而至其究竟成就處。專以聖人繼天之所不能言之。則善惡旣分以後。有若天理無如之何者然。夫有必然而不可易之妙者。是理也。豈其如是之不能。而一任他聖人繼之歟。此則未見先生定論。稟質之如何。嘗見農巖先生雜識。有一段語。似甚的確。錄呈擧似仰稟。如何。農巖曰。事有萬殊。而至善之理。無乎不在。或疑人之不善。安有所謂理。曰。指其事而言之。雖不可謂之理。然善則治。而不善則亂。善則安。而不善則危。善則吉。而不善則凶。非理而何。是則事雖不善。而理之至善。固未嘗不在也。竊嘗因農巖說而思之。治亂安危吉凶。皆理之所有。而善則治。不善則亂。善則安。不善則危。善則吉。不善則凶。天也。理之必然者。而卽所謂至善之無乎不在也。善而治。不善而亂。善而安。不善而危。善而吉。不善而凶。人也。天亦無如之何。聖人之所不能。其在斯乎。答曰。理有必然之妙。無能然之力。故聖人繼天之所不能者常多。必欲取證先生聖人制律之訓。盡之矣。盛論中。引農巖說云云。已躍如。善則吉。不善則凶。莫非天理。而聖人取其善則吉者。去其不善則凶者。使天下之事。必皆止於至善。是非繼天之所不能乎。以愚之踈畧。不欲更稟。
厚允曰。十世可知章。師門答條中。朱張兩說孰優。正好想量。想已經商量。果孰優。愚意南軒據秦氏而言。朱子據事理而言。言各有當。盖損益者。因其故而損之益之之謂。若秦氏之心。自以爲功過五帝。德兼三王。三代不足法。一切掃除。創立新制。曷嘗有因周之故。而參酌斤兩之心。南軒所謂廢先王之道。而一出於私意者。得秦氏之心。雖然據理而言之。則其大體。秦氏終泯滅他不得。且其焚坑。因周末之繁文而然也。其強戾。因周末之柔弱而然也。周之衰。諸侯擅命。故彼因而廢封置郡。周之衰。君弱臣强。故彼因而尊君卑臣。其所以創制。亦不出因而損益之而已。朱子所謂損益太甚者。畢竟得之。未知如何。損益之未盡善。未盡善三字。非朱子本語。本語只曰損益得太甚耳。未盡善云者。善而未盡也。秦氏之所爲。何善之有哉。或未及細考而然耶。抑別有微意歟。答曰。愚之所問。不在秦氏損益如何。但願聞朱子非南軒之意耳。若夫秦之損益。朱子已詳言之。來示皆是也。何必多及。答語中未盡善三字。恐當時禾暇考朱子說。雖更稟。似無他義。
厚允曰。老兄問目。論語知十章集註。卽始而見終。因此而識彼。二而字。亦改作以字然後。合於本文之意云。卽因兩字。已有以字意。又以以字承接之。則語意無乃重複乎。更詳之。又本文同一以知字。而集註於知十。則曰卽曰見。於知二。則曰因曰識。皆自金秤上稱出來。恐加減不得。答曰。來喩甚精。厚允曰。老兄問目中。廟火焚。神主當題於廟墟云。則題於墓所。何獨不當。以其魂返於室堂。而廟墟乃其所嘗憑依之地耶。雖嘗憑依。而今已災矣。精靈飄蕩。而不復憑依。又何必於廟墟。吾聞之。子孫之精神。卽祖考之精神。子孫之精神集。則祖考之靈感應而聚焉。苟能致吾誠。會吾精。而設奠以題之。則無處不可。而況正寢。乃子孫之所嘗會精處。祖考之所嘗感應處。題於正寢。恐最當。更詳之。答曰。雖蒙盛喩。愚見依舊未回。何者。正寢固是子孫會精處。祖考感應處。然若乃廟墟。則平昔精靈依憑之久。雖有一朝之變。必有彷徨眷戀於此。而湊泊於此之爲易矣。不於此處而更於何求。故曰。愚意題於廟虛。似當。
厚允曰。老兄問目中。遞遷時如有祔位。則祔主亦隨之云。此一節。與備要不同。恐不可猝乍句斷。備要曰。本位出廟。則祔位當埋墓所。盖祔位與正位。少無隆殺之節。不亦未安乎。備要之意。恐以此也。又按程子曰。下殤終父母之身。中殤終兄弟之身。上殤終兄弟之子之身。成人而無後者。終兄弟之孫之身。此四頃祔祭。各有代限。今隨本位。而遷於他房。亦非程子之意。或曰。祧遷必於親未盡者。則其祔位亦遷於兄弟之孫若子。何獨以兄弟之適孫死。而兄弟之諸子諸孫。不敢復祭父祖之兄弟乎。程子言兄弟之孫。何嘗單言兄弟之適孫乎。何必謂非程子之意耶。曰。子之言似矣。而中殤終兄弟之身。若兄死。則又遷而之弟房耶。上殤終兄弟之子。則若長子死。又遷而之衆子之房耶。殤祭之遞奉。愚未知其必然。此而不然。則其言兄弟孫之身者。恐亦一例也。更容商量。如何。此非論禮意而已。鄙家有祔位。竊欲講定以竢後日之行耳。答曰。愚聞本未之有考。備要旣有本位出廟。祔位當埋之語。則此不必更稟。
厚允曰。師門答條中。發者氣也一句。自先賢已有此語。而愚尋常疑之。請以諺吐解之。以發其所以疑之意也。若曰。發ᄒᆞᄂᆞᆫ거슨氣也云爾。則其於所謂在中之理。發形於外者。不啻相戾。而大本達道。判爲二物也。若曰。發케ᄒᆞᄂᆞᆫ거슨氣也云爾。則其於所謂氣是關棙者。雖是相孚。然其語意氣象。歸重於氣。而有若氣使理也。以此以彼。皆可疑也。今先生亦曰云云。未達其意所在。答曰。先生答語。結尾云伊川之意。或以是耶。或字耶字。亦是先生疑辭。而伊川說終有可疑。至若發者氣也以下盛論云云。剖釋精微。可見吾兄兄得此理。徹底洞然。然以愚見言之。則此不必深疑。發者氣也此語。先賢本非單句獨立說來。而乃與所以發者理也一句。雙立對說下來。則不害氣爲理之用也。豈疑氣之使理也。盖能發者氣也。所發者理也。理乘氣行。如人乘馬行。旣曰人乘馬行。則這箇行者。固歸宿於人字分上。然其運脚者。馬也。故曰。行者馬也者。未爲不可。今有人乘馬行。而汎言其行。則必曰人行。盖馬之行。卽人之事故也。若就這裏。分言所乘所行。則乘者人也。行者馬也。發者氣也。其義與此相似。未知何如。
厚允曰。老兄問目中。木性仁金性義云云。或見此段。指而問余曰。性是理之結褁。故謂之木性則不可。此非可疑耶。凡有形氣之物。莫非理之結褁者。而有是性焉。故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。朱子亦言灰土之性。金木獨非有形氣之物而理之結褁者耶。余應之曰。非是之謂也。木之理。人得之而爲仁。金之理。人得之而爲義。所謂結褁也。人物之生。稟五行之氣以爲形。得五行之理以爲性。五行是分共底。人物是結褁處。故云然爾。鄙答如此。果不失於先生本旨耶。答曰。吾兄答人問。深得先生本旨。但公共二字。改作流行字。何如。問鄭時林講目中。陰陽上各有陰陽。以晝夜言之則云云。末段以本原言之。則萬物之理。卽一物之理也。以分殊言之。則一物之理。卽萬物之理也云云。一物之物。似是病。才言物。便是分殊。本原上。豈有物之可言耶。直曰以本原言之。則一理也。以分殊言之。則萬理也。似好。厚允答曰。以本原言之。則一理。以分殊言之。則萬理。此二句。出於兄口。吾活看。而若出於世儒之口。則此便是爾一我殊之論。萬一各占一位。可乎。盖世儒之論。以人物性。爲已落分殊。不足爲一原。故別求一原於空蕩蕩地位。先師所以極力辨破者在此。才言物。便是分殊。亦同一伎倆。伯彦之言有曰。一物之理。卽萬物之理。而不曰一物卽萬物之理。則其所言物者。非論物也。乃所以言理也。然則兄所謂本原上。豈有物之可言云者。不幾近於謾罵歟。夫理擧着。都無欠闕。故曰擧着。一枯木一微鹿之理。便都在這上。而枯木微鹿之理。便是兩儀四象八卦之宗祖。兩儀四象八卦之宗祖。非本原而何。本原上言物。固不可。而獨不可言物之理乎。
問閔致完問傳十章字字句句云云。又問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云云。李熙容問所補第五章云云。又問平天下以心推之云云。此四條。恐刪之不妨。厚允答曰。閔問第一條。刪之固好。其餘三條。恐不必刪。雖於經旨無甚發明。而顧問者淺近耳。隨問而答何害。亦足以見因材之篤不倦之意也。下鄭禧源問答。除首除腰。亦同。
問錫龜問目中。所謂沖漠無朕。萬象森然已具云云。隨成萬般不同之物則云云。則字上。兄更加然字。加一然字。則以上文脈不屬。去然字。則以下意味無害。然字刪去。似好。厚允答曰。去然字。則是一直說去。加然字。則是再轉結來。語意恐尤確。然則字。與如此則若是則同義。然此等增刪。無甚利害。
問錫龜問目中。或問費隱章小註云云。此條當刪。厚允答曰。此條何故欲刪之耶。兄意未達。實有此理。而且肚裏外皆是水一句。說得最好。
問錫龜問目中。有君喪服於身云云。此條當刪之。厚允答曰。此條恐亦不必刪。此問本非淺問。又大義所係。何可剛也。
問錫龜與申鍾求論太極因云云。火金土之圈。莫不皆然。而下兄更添才有一行便有五行則此亦統然也十四字。語非不好。理非不然。然五行之圈。周子旣已分作五箇圈。而分書五行字。則此五圈。當分作五行之各具看。不可作統體五行看。故愚止曰。木之圈。萬木之統體。水之圈。萬水之統體也云云。若如兄言。則此五圈。各各統體五行。而未見各具之義。似乎未安。厚允答曰。若只論五行圈。則五行圈。是各具也。兄教當矣。乃兄所與申論辨者。則是明統體各具。不可分而爲二之論也。故兄所謂萬木萬水云云。就各具。言其統體也。旣就各具中。言其統體。則木之一圈。非但爲萬木之統體。水火土金便在這裏。理無盈縮故也。卽所謂枯木微塵之理。便是兩儀四象八卦之宗祖之說也。若只曰萬木之統體。而不言才有一便有五之妙。則所謂統體者。箇箇分片。而水火金木各有窟穴。非所以明統體各具之不可分而二之之故也。意兄非不知此。而特偶未之及。故妄下一語。以補其不備耳。然因兄教而思之。所補語欠曲折。致兄疑問也。謹改如左。更詳之。若各具之義。則兄所謂惟五行圈則各具也一句。已盡矣。其末結句。亦未穩。竝改之如左。火金土二之圈皆然。莫非統體也。又才有一行。便有五行。統體不可外各具而求之。各具之太極外。更別無一層統體之太極也。
問鄭禧源問答葉味道書云云。此條未達其意。厚允答曰。考葉味道問目。則可知也。葉問女子適人。爲父母朞。不貳斬也。賤婦喪母。旣葬而歸。繼看喪大記曰。旣練而歸。賀令反終其月數。誤歸之月。不知尙可補塡乎。因思他人。或在母家。彼此有所不便。不可待練。不可不歸。又如之何云云。故朱子之答如是。禧源擧答語中衣服則不可變一節爲問。故先師之答。又如是耳。然其所謂未奔喪三字。未穩。改以未歸。則好矣。
問錫龜問目中。有檀弓。夫子曰。始死羔裘玄冠者。易之而已。以此觀之。黑笠似去答語。以文義觀之。則羔裘玄冠。非常着衣服云云一條。似當錄於遂庵曰吉冠云云條下。而不錄。何也。厚允答曰。所謂易之者。恐與表記所謂易服同義。卽所謂始死鷄斯之義也。與下文夫子以弔。所指不同。雖一處幷言。而實是兩事。如是則所問所答。恐未襯切。故刪之耳。
問鄭載圭問目中。或問祖喪中父喪。則爲祖服制云云條。通解所引服令云云。嫡子兄弟未終祥而亡。兄弟二字衍問者。旣曰受祖服。則平居常以何服。答父服爲己而製也。祖服爲父而製也。饋奠時則各服其服。常居則持己服。持己服一句恐不然。旣曰。父服爲己而製。祖服爲祖而製。爲己而製。己行己事也。爲父而制。代行父事也。己事父事。輕重逈別。常居恐當持祖服。厚允答曰。盖因服制。今本文而然耳。然兄弟二字。非但爲衍而已。實乖於立孫之禮。謹當刪之。因兄教而得此新意。多謝多謝。兄之所聞者。旣如此。愚之所質者。又如彼。而各有成說。各有意義。令不敢遽然從違。然未知子之所以代父者。以祭奠之不可無主耶。退溪沙溪。皆以祭奠爲言。而曰不得。不服其服而行其禮也。愚所謂恐合於退溪之意者。以此耳。若常居。則己行己事時也。恐不可曰代父而常居也。更以見喩也。大抵兄我所聞。不同如此。必有一誤。而今稟質無地。樑摧之慟。於是爲切。抑各是一說。俱無害於禮意耶。此等處。兩存之無妨。兄我往復櫽括成文。祔之於下。如何。
問錫龜問目中。繼室與前室。爲一人也云。一身之身字。兄換作體字。體字固無分殊。然細察字義。則無分殊之中。有些分殊。而一身之云似近。盖一身云者。代身之謂。非同體之稱。未知何如。厚允答曰。曰一身。則兩人便成一人。而未見其人各有身也。曰一體。則人各有身。而其體則一也。此體字。自有來歷。曰實具三年之體。曰繼體。曰正體。非身體之謂。猶言體段體統體禮也。盖繼室雖代前室。便謂一身。則恐未然又代身二字。話頭不雅。
問鄭義林問目中。勸漢祖云云。鄭時林問目中。秦始皇晉元帝云云。又賈誼云云。此等條刪之。恐無妨。厚允答曰。賈誼云云。果如兄教。而上二條。愚未見其可刪。盖勸漢祖一着。旣有程子之論。後來無人敢議到。而季方所謂。無文王之德。爲他日生靈之患數語。可謂極窮到底。而是求有成之心。非公心也二句。恐非先生。不能答也。與夫子民無信不立。孟子行一不義得天下不爲。董子正誼明道之說。同一心法。吾儒之根本在此。何故欲其刪去也。至於秦晉。則言之雖甚醜。史記所傳。旣如彼。人多疑之。非獨伯彦。此皆世俗繳繞之見也。雖無足道者。然旣擧以爲問。則答是也。亦難矣。欲詳言之。則有若爲秦晉分疏煩而費辭。欲略言之。則意未達。不足以解問者之惑也。大非事理四字。辭約意備。恐難如此下語也。
問小記。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。父稅服。而已則否云云。此條愚意以爲。祖父母諸父昆弟之喪。以其生於他國。不及識之。故不爲追服。於天理人情甚遠。故不取註家語。疑其爲死生異代者也。而兄意恐是經文兼言昆弟。則弟於已無先代而生死。故刪之。然弟字恐是昆字帶來說。不以文害意。可也。未知如何。別有精義。勿惜誨語。厚允曰。此本草不在。今不追憶。是以不敢下說耳。本草投示。當更思。
問向因錫龜問目中。見得道理無空闕。故不可須臾之語。因語及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。其時兄言。今不能記得而似謂道於天地不可須臾離。當時愚於昏迷中。未及詳辨隨而應諾。然以愚見。則兄言終是未安。愚則以爲此謂人於道。不可須臾離也。若謂道於天地。不可須臾離。則不惟於率性修道。意不相續。不可二字。又非所以語此。若如兄言。則子思必別爲立言。必不曰不可也。且章句所謂所以不可須臾離。若其可離。豈率性之謂哉。與夫或問所謂由教而入者。其始當如此之語。皆非人於道不可須臾離之謂耶。道理無空闕處。卽章句所謂無物不有。無時不然之謂也。故字卽所以二字之意也。故此故字。不必移在離字下。厚允答曰。曩時吾所云云。吾亦不能記得云何。然道於天地不可離一句。實非吾言。集註分明以率性而言。何故更尋那天地說去。使道爲空蕩蕩物件耶。雖然兄我所爭。只在主道主人之異耳。兄則曰。人於道不可須臾離。是所主而言者在人。我則曰。道於人不可離。是所主而言者在道。姑置多少引證。只就子思本文。而觀其語脈文理然後。參以章句。則似可以解悟。何哉。以道也者發端。而曰不可須臾離。此非主道而言乎。君子戒愼以下。方始說人於道不可離也。中間是故。所以明道固如此。故君子必如此之意也。章句所謂所以不可須臾離。所以二字。亦主道而亦主道而言。明其道於人不可離之故也。至下文所以存天理之所以字。方說人之體道。而中間是以。應本文是故二字。兄所引或問由教而入云云。乃是君子戒愼以下。而言必欲於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一句內。便主人而言。使上下句。渾無節拍。未可曉也。至若故字之移置離字下。亦極費商量。若故字依舊置空闕處下。則必削去見得二字。方成文理。若見得字及故字皆依舊。則下句不可之可字。當删改。若削那見得字。則道理無空闕處。卽章句所謂無物不有。無時不然者也。故字卽所以二字之意也。果如兄教。而却不削見得字。移置故字者。盖以兄問目中。說中庸君子戒愼工夫。不可須臾少忽之意已盡故也。盖由君子所以如此者。正以見得如此故也云爾。合問答而觀之。可知矣。願兄細思之。若以爲未然。則更以見諭也。
問伯彦講目中。夫婦有別。禮也。長幼有序。智也云。鄙意長幼有序。禮也。夫婦有別。智也。二程全書中。有禮別也之語。先哲固有以禮爲別。然此不以夫婦有別言之。若就五倫上言。則有序似當屬禮。有別似當屬知。厚允答曰。愚從兄說。
問伯彦講目中。惻隱之有節文者。則禮也云。鄙意西端。是就情發處言。節文當於行事看。方論四端。而遽及節文。無乃迂遠乎。愚意。則以爲凡發一情。其發動者仁也。合宜者義也。中節者禮也。知覺者智也。誠實者信也。則似庶幾。盖中節與節文。語目不同。中節云者。情之發無過不及之謂也。節文云者。不可直情徑行。撙節回互之謂也。禮之有節文。吾非不知。但不當於情發處言之。厚允答曰。此有朱子說。曰燦然宣著者。禮也。兄以節文謂當於行事看。則兄所謂中節之云。抑外節文而別有他歟。有言天理之節文者。未有言人事之節文者。盖天理有自然之節文。故人事循而有儀。則所謂率性之謂道者也。何獨於人事上看乎。愚意有是節。而方言中無是。則中無可言之地。中庸所謂中節。雖不竢人安排。然猶是就發後言之。獨可言於情之始發。而却不可言抑。何歟。節文中節。非有兩箇。就他有條理次第。而無過不及而言。則謂中節。以此論之。伯彦之論。猶或近之。而兄所言。未可曉也。雖然才說節文。便有節有文。而色相太露。言之於惻隱之發。則亦未保其洽當。只得遵守朱子說而已。不必更有他說話。
問伯彦講目中。人物性同異。引朱子諸說以爲此言人物本性之不同者。可疑。盖此數段語。皆理則本同。因其氣稟之不同。而人物之性。有不同之謂。非人物本性不同之謂也。今乃就因其氣稟而不同處。以爲本性之不同者。何也。朱子旣曰。人物性本同。又曰。以理言之。則無不全。三色椀中所放。只是此水。長短隙中之日。只是此日。則此非理本同之謂乎。故以爲此言人物之性不同。則可也。如曰人物之本性不同。則不可也。本性四字。似非見理之言。本性云者。就氣稟中挑出。而單指理言之。朱子所謂天命之性。通天下一性。何相近之有言者是也。相近旣不可言。則不同其可得言耶。陰陽五行。各是一氣所稟。而性則同。朱子此語。亦人物性同之謂也。而竝與已上諸說。同謂人物本性不同之謂。則又可疑也。盖此理之外。更無他理。故單指理而言其本性。則人物之性無不同也。人物旣生。則氣稟不同。故兼氣稟而言其所賦。則人物之性。各不同也。厚允答曰。主同者。言同而不言異。主異者。言異而不言同。此湖洛之所以分也。抑未知兩兄之所言同者。同而無異。所言異者。異而無同歟。伯彦吾雖不保其何如。而老兄則吾保其有見於同而異。異而同者。而今看云云。乃不過誦洛下諸儒已成之說也。誠竊訝惑。抑伯彦說得偏。故兄欲救其偏。而語有不備耶。兄所言不同處。皆歸咎於氣。而曰因氣而不同。重言複言。而更不言本分不同。若是則爾一我殊之論。先師苦口極論。以幸萬世者。不待一再傳而已。壞爛耶。甚可懼者。然兄豈然也。是必有其故。而未得面請曲折。可恨可恨。
問伯彦講目中。從其氣之發用底如彼。而識其隱微底理亦如彼云。理亦如彼之亦字。有些未安。何者。凡理之流行發用也。理本如此。故氣得如此。非氣自如彼。故理亦如彼也。理亦如彼四字。使知者觀之。則固無病敗。若不知者觀之。則其語勢所重。歸在氣字上。似乎氣能如彼。故理又如彼。氣爲之主。而理隨而然。轉入於主氣之歸矣。此故亦字。換作本字然後。其語意方得顚撲不破矣。吾兄豈不知此。恐於下語之際。偶未之察。故瞽說及之。厚允答曰。兄言甚確。無容更評。
問伯彦講目中。太極圖五行圈。盖以圖說五氣順布立言云。五行之圈。盖以圖說陽變陰合。而生水火木金土之意。對待立象也。
問伯彦講目中。當然必然能然將然自然。皆理之名也云。此皆理之事。非理之名也。
問伯彦講目中。費與隱皆理之名也云。道之體。微而無形像。故曰隱。道之用。廣而無不在。故曰費。費與隱。皆理之實。非理之名也。
問伯彦講目中。中亦理之名云。中者。無過不及之名。非理之名也。問伯彦講目中。中是性之異名。和是道之異名云。中非性之異名。狀性之體也。和非道之異名。形道之用也。
問伯彦講目中。喜怒哀樂。氣也。又曰。情。氣也物也。中和。道也則也云。喜怒哀樂。理之乘氣而發也。非氣也。情是性之用也。性是情之體也。情之發也。其發者固氣也。發之者卽理也。故情之爲情。其骨隨血脈。歸重在理。而不在氣也。至其不中節處。乃氣之爲耳。今乃專屬於氣一邊器一邊。不亦冤乎。中節之爲言。只此理之發。而直遂無過不及之謂也。今乃就其中。截斷得不可截斷處。分開作道器物則看。則未知子思立言之意。然乎否乎。若欲於喜怒哀樂上。分別箇道器物則說下來。則能喜怒哀樂之氣。器也物也。所以喜怒哀樂之理。道也則也。情與中和。不可分道器物則看也。彼以和爲氣者。其病根在於何處乎。不在於認情爲氣耶。吾兄亦以喜怒哀樂謂之氣。則反爲助瀾其說。安得折彼之口。而服彼之心也。
問伯彦講目中。中節之和字。非時中之中乎。時中之中字。謂之理可乎。謂之氣可乎云。此語亦有未安。中節之和。固時中之中。而以和字。爲時中之中。則不可。時中之中。固理也。而以中字謂之理則不可。故此兩箇字刪去而後。語意無病。厚允答曰。此上七條。皆從兄說。【己上。因法和講錄。而有此往復。】
問顔淵曰。如有所立卓爾。雖欲從之。末由也已。詳此語意。卓爾二字。似指聖人而言也。性理大全朱門人問。所謂卓爾之地。乃是廓然貫通而知之至極。與聖人生如意味相似否。朱子曰。也是如此。以此觀之。則卓爾似是顔子自謂。盖卓爾聖人。而顔子已知得到。故云爾耶。厚允答曰。朱門問答。非全指顔子而言。泛論學而至於卓立之地者耳。若論語。則分明指聖人。
問朱子曰。天將降非常之禍於此世。預出非常之人以擬之。此語可疑。厚允答曰。日將降。曰豫擬。其語意有若有所爲而爲者然。故兄疑之耶。自天言之。則固莫之爲而爲之。自人觀之。則其準擬巧湊。實若有爲者然。朱子之言。乃自人觀之之說也。天下之生久矣。一治一亂。未有往而不復者。今天下亦有豫出而擬之者耶。何其降禍之此極也。噫。
問先師偶記中曰。挑出四端。而謂之理發。則外此七情。乃是情之奔逸。七情豈可盡謂之奔逸耶。恨未質正於當時。厚允答曰。單言七情。則七情有善有惡。對四端而言七情。則七情乃是情之放逸者。盖單言七情。則四端在其中。對四端而言七情。四端乃其就七情而剔發出者也。所謂子先獲珠所餘鱗介耳。嘗以此仰稟。則先生頷之。因微吟旣挑出四端。而謂之理發。則外此七情。乃是情之放逸者一段語。盍於挑出外此四字仔細看乎。書成後。復思之。致疑於偶記中一段語者。盖亦有意。大抵四七非兩情。理氣無互發。然畢竟面貌不同。苗脈亦異。以七情便謂之專然不善。或涉過重。卽所謂人心。不可便謂人欲之說也。然朱子以七情爲氣發者。非以七情之發。別有一塗而言也。其理之乘氣而發一也。而爲氣所揜。而氣反重。故謂之氣發。爲氣所掩。而氣反重。則謂之放逸。亦何害。此與人心道心之分。煞有分别。人心之生於形氣。自發之機而言也。七情之爲氣發。自發之後而言也。是以愚嘗曰。四七皆理之發。而氣發云者。自已發後去見他如此。先生手自點批曰。甚合吾意。更加細思。如何。
問李鏡湖曰。妾子於父死。承重而後。方爲其母緦。若父在。則只當爲父母喪之杖期也。此言可疑。旣升爲嫡子。則名分已定。於所生母降服。似不分父之存没也。又曰。承重妾子。於所生母除服。無別祭而別室奉几筵終。三年行大小祥。恐盡於人情。此說可疑。除服後。豈復有大小祥也。但几筵不必掇於三年之內。忌日只設祭。恐當。厚允答曰。此兩條。李氏恐誤。
問來後於所後祖喪期年內者。芝村。則以爲似與服未盡前聞喪者同。自今服朞。至明年除服。似宜。陶庵。則以爲可以己未生前已没之事爲準。未出後而在本生家者。便可與生於他國一例看。愚意恐當從陶庵說。厚允答曰。此恐不可若是斷言。祖與父期三年。輕重雖殊。其義例一也。爲後於父喪三年內者。更制遠月。已有定論。獨不可推之於祖乎。若以未生前已没爲準。則父喪後爲後者。亦以遺腹兒處之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