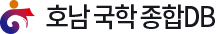- 국역/표점
- 표점
- 대곡유고(大谷遺稿)
- 卷之四
- 雜著
- 師門問答
대곡유고(大谷遺稿) / 卷之四 / 雜著
師門問答
問太極動而生陽。靜而生陰。太極理也。陰陽氣也。氣則動靜。而理不能動靜。然理有動靜。故氣有動靜。太極之有動靜。是天命主宰處否。先生曰。見得精密。
問先生答權信元書有曰。太極單指理。固然。陰陽單指氣。是果成說乎。太極固可謂單指理。則陰陽豈不可謂單指氣。先生曰。此非可疑之說。易以道陰陽。人必曰易理。何也。
問前賢有曰。未發之中。只是吾心統體一太極。不可喚做理之一本處。易有太極之太極也。易有太極之太極。水之本源也。吾心之一太極。水之在井者也。事物之太極。水之分乎器者。此論。似以易有之太極爲上一位。吾心之太極爲中一位。事物之太極爲下一位。分作三層說。竊有惑焉。天地萬物。只是太極中物。如魚在水中。肚裏肚外皆水。鯉魚肚裏水。卽鱖魚肚裏水。然水物也。故萬斛水不能盡在一魚腹。太極大而天地。小而一物。所具此理。無一毫有餘不足。終始只一箇太極。豈有上下彼此之間也。先生曰。太極云云。前賢所論。果可疑。
問景鍊曰。理與氣不離處。必以不雜言之耶。錫龜曰。氣則有質。理本無形。旣無其形。何嘗有離。何所有雜。所謂不離。非混淆。所謂不雜。非各立。理與氣不離而亦不雜也。先生曰。子之見似精。
問周子曰。太極動靜而陰陽生。陰陽一太極也。夫陽爲善。陰爲惡。而太極乃陰陽之妙也。又曰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。以孟子所謂性善。乃若其情。則可以爲善。與乍見孺子入井。怵惕惻隱者觀之。分明是性本善而無惡。周子該理之本末始終而言之也。孟子擧其體面而言之耶。先生曰。體面二字。甚生且弱。恐是自家所見。未甚明的。故爲此籠罩語。更就繼之者善。大哉乾元。萬物資始。一陽初動處。萬物未生時等語。着眼目。知元初無有不善然後。孟子道性善。眞實不爲虛誑。
問沖漠無眹萬象森然已具。若謂世間萬有皆本具於沖漠無眹之中。而沖漠之中。具萬象之理。故各生萬端不齊之氣。隨成萬般不同之物。則世間好事不好事。均是各得太極中本具之一象。是沖漠之中。善惡混雜。太極不得爲純善無惡矣。先生曰。世間本無不好事。所謂不好事。好事之未成者也。
問若謂已具者。具純善之理。而有此理。則生此氣。此氣旣生。變化萬段生出。世間萬殊之事物。其善者根於理。不善者作於氣。則是造化之妙。半是理使氣。半是氣屈理。太極不得爲萬化主宰。先生曰。爲昧者言。不得不曰。善者根於理。不善者作於氣。若論造化根本。則別是一說。
問先儒云。理之有善惡。因氣而有。然凡天下有形質者。或因氣而變。惟理初無形狀方體。聲色臭味。只是其所以然者。而有必然之妙也。天下無理外之物。故事之萬殊。非理因事而殊。乃事因理而殊也。然則氣之或純或駁。必有所以然與其所必然者。故曰。善惡皆理也。形質一定不可變。理無形。故因氣而變。氣之有純駁。以其往來屈伸。雜錯不齊。而理在其中。故隨而或有不善。何謂善惡皆理也。曰。自揚子雲稱善惡混。獲罪於聖門。以後人雖至愚。孰肯言理有惡也。然物之有形質者。大如天地。時有消盡。安有有形質而不可變者。惟理也。不以有是物而存。不以無是物而亡。先天地而無始。後天地而無終。卓然乎事物之表。常行乎事物之中。萬事萬物。一動一靜。莫非此理之所使。而氣之往來屈伸。雜錯不齊。其主張而使之者理也。故其粹其駁。先有此可以粹駁之理。若謂理本純善。因氣之有粹駁。而隨以善惡。則不惟氣不本於理。所謂理者。只是柔軟無骨底理乎哉。盖自孔子言。繼善成性。孟子道性善以來。孰不曰理本純善。而吾之爲此說者。思之不得。故盡吾之疑。欲眞知理之純善也。先生曰。先哲言。善惡皆大理。正是說到此處。今以實事言之。則所謂理者。不過陰陽之妙也。下面陽爲善。陰爲惡。陽爲君子。陰爲小人。謂之惡不根於理可乎。故說理不如說中。中則無不善也。從上聖賢。曰中曰衷曰則曰彛。未嘗一言及理。後世之論。則中衷等字。變而爲理字。可以善看。不可以不善看也。最有一事可證。嚮者天下之萬聲。無非太極中分出來者。而聖人制律。只用黃鍾一聲。此天地之中聲也。曰中曰衷。其曲折如此。聖人繼天之所不能。其在斯乎。
問或曰。子嘗以爲善惡皆根於理。氣之有粹駁。以其有所以然。然則先儒所謂氣有清濁偏正之殊。故理隨而萬變之說。皆可廢歟。曰。自源頭處觀下。則理本生氣。自流行邊說去。則氣或害理。吾所嘗言者。原頭處論也。子所擧者。流行邊說也。其曲折。則非一言可了也。先生曰。此段與鄙意合。近世議論。每將流行邊說。攙入原頭。
問或曰。子嘗曰。凡氣之所爲。皆理之所爲。而善惡皆根於理。以此言之。則理本有善惡。又曰。就原頭處論。理本生氣而皆善。自流行邊說。氣或蔽理而爲惡。以此言之。理本純善。因氣有惡也。曰。所謂理者。萬事萬物不得不然之故也。故曰氣之所爲。皆理之所爲。而善惡皆根於理。理只是所以然之妙。未有所能然之力。故氣之流行變化也。或承順而遂其善。或掩蔽而反爲惡。其蔽之者。非氣自爾。亦理之固然。雖固然而非理之本然也。先生曰。大槪非不是當。但其意味牽強。無融釋脫落氣像。殊與吾友前日見解不同。無乃更數長廊柱而錯耶。須知善惡皆天理云者。不是兩端各立。各自出來。正以天下本無惡。而所謂惡者。乃善之孼子。則都無事。孼子未嘗非己之血脈。故惡亦不可不謂之天理。如斯而已。
問天所賦爲命。物所受爲性。譬如雨之注下虛空中。則謂之雨墮。在平地上。則謂之水。先生曰。然。
問此理在天地。則曰天地之性。在人物。則曰人物之性。就人物上兼氣質言之。則曰氣質之性。單指理言之。則曰本然之性。先生曰。天地之性。謂天地所賦與人物者耳。非謂在天地也。
問朱子辨胡氏心無死生之說曰。天地生物。人得其秀而最靈。所謂心者。乃虛靈知覺之性。猶耳目之有見聞耳。此性未達其義。曰虛靈知覺之體。則如何。先生曰。此性字。乃自然具足之意。非指人生而靜以下也。
問人與物均得太極五常之德。故曰性同。人得人之理爲人。物得物之理爲物。故曰性異。先生曰。論人物之性。大槪則然。而恐未爛熟。且置之無妨。
問高峯先生論本然氣質之性曰。孟子剔出而言性之本然者。似就水中。而指言天上之月。伊川兼氣質而言者。乃就水中。而指其月。此言不能無感。嘗以爲本然之性。就水中。單指月言之。氣質之性。兼水而言之。非有天上水中之分。先生曰。天上之月。水中之月。月有天水。而理豈有天水。惟理無對譬。辭安得逼肖。惟在觀者善觀耳。
問錫龜以爲本然之性。單指理言之。氣質之性。兼乎氣言之。故未發之前。亦有氣質之性。鄭載圭鄭義林以爲。此性墮在氣質之中。而有氣質性之名。則兼氣謂氣質之性。非爲不然。而若於未發時。謂有氣質之性。則恐未然。先生曰。景範之說。是南塘餘論。此處極精微。非卒乍所可剖判。盖性本屬未發。而未發字。與中庸未發之中相亂。未發亦有氣質。則未發不可謂中。氣質與生俱生。則亦不可謂未發。時無氣質。將何以折衷哉。盖衆人未發。非眞未發。不昏則亂。以此境界言之。則未發亦有氣質。孰云不可。若或有澄然未發。則此乃湛然之本體。偶然回淳者也。此乃天下之大本。又欲將氣質二字。藏在這裏者。不已病乎。當細細商量。不可卒乍剖判者。此也。
問氣質之性此性字。不須深看。似是俗語性勤性懦性剛性柔之性。未知然否。先生曰。然。
問天地亦有心乎。曰。人物之心。得天地心來。天地若無心。人物豈有心也。或曰。天地之心。亦有知覺乎。曰。人物之心。自這裏而有知覺。則這裏自有本然之知覺。曰。天道福善禍淫。是無心而自來耶。有意而必然耶。曰。謂之無心。太冷淡。謂之有心。則穿鑿。然終不是無心。先生曰。然。
問申鍾求曰。天地有無心。有有心處。曰。天地之有心處無心處。朱子已言之。曰。須要知得他有心處。又要見得他無心處。有心處。其所謂若果無心。則牛生出馬。桃樹上發李花是也。無心處。其所謂四時行。百物生。天地何所容心是也。其意盖本有主宰。而元無容心焉。雖無容心。而實有主宰之謂。尊諭似謂有有心處。有無心處。何處是無心。何處是有心。宋時一曰。有心無心處。似於體用上看。曰。然則有心處爲體。無心處爲用耶。抑無心處爲體。有心處爲用耶。愚意以爲本有主宰。而元無容心。故曰無心。雖無容心。而實有主宰。故曰有心。恐不可以有無分體用看。先生曰。子之言是。
問朱子曰。天地之心。不可道是不靈。但不如人恁地思慮。恁地思慮。此乃人不及天處耶。先生曰。恁地思慮。此乃人不及天處。其說甚善。
問心是五臟之一。而虛靈之亦名曰心云云。先生曰。吳臨川說。固可笑。而君之所言相似二字。亦甚病。虛靈之必名曰心。明指血肉之心言。非但相似而已。其得名苗脈。吾亦每取康節心屬火之言。亦不須深看致生病敗。
問先賢曰。四端卽道心及人心之善者。此言尋常未達。先生曰。道心人心。苗脈各異。人心之善。卽道心爲主宰而然也。四端以道心看。似當。
問或曰。寂然不動。性也。感而遂通。情也。曰。寂然不動。則性存乎這裏。感而遂通。則情行乎其中。而能寂能感。心也。寂然感通。當以心看。或曰。性。理也。心。氣也。情。理氣之流行也。曰。心與性對擧。固有道器之分。性與情是一理。而但有體用之殊。盖心。氣之靈。性。理之在中渾然者也。情則乘氣流行者也。先生曰。答說皆是。
問感應一理。而形器不能間隔也否。先生曰。本同一氣。故有感應。此感應之理也。感應本旨。當屬氣分。
問或曰。力生於氣。曰。力生於質。質生於氣。或曰。氣壯者。力宜強。氣孱者。力宜弱。而或有力贍而氣易耗。有力微而氣常旺者。何也。曰。此乃氣有剛柔。而稟有多少故也。盖稟剛而多者。氣壯而力強。稟柔而少者。氣孱而力弱。稟雖多而柔者。力雖贍而氣易耗。稟雖少而剛者。力雖微而氣常旺也。先生曰。然。
問或問氣之所運。必有以主之者。朱子曰。氣中自有個靈底物事。靈底是理否。先生曰。有理故靈。而不可謂靈便是理。盖此處小差。則入於認氣爲理。
問朱子曰。木神仁。金神義。仁義理也。神氣也。則當曰木性仁金性義。而曰木神金神。何也。先生曰。神氣也一句。似誤。理之妙處。謂之神。理之不神。則是木強一塊矣。易大傳陰陽不測之謂神。横渠曰。兩在故不測。兩在者。旣在陽。又在陰也。所謂在者。非理在乎。木性仁之語。可笑。木亦有惻隱之心乎。
問木神仁。金神義。前者誤以神爲氣及得理之妙處之訓。此固無疑。然神是理之妙處。性是理之渾然。神與性均是理。而木金之神。旣謂之仁義。則木金之性。不可謂之仁義耶。先生曰。神是理之運用。故謂木神則可。而謂之木性則不可。
問人有曰。鬼神吉凶禍福。只是以理言。理無不善。人能順理則吉。逆理則凶。自是理合如此。安有所謂鬼神一一降之哉。朱子答曰。是也。然福善禍淫。只是理合如此。而無有所謂鬼神之爲之如問者之說。則其說似乎太冷淡。凡天下萬事。理合如此處。鬼神合如此。而所以然者。理也。所能然者。鬼神也。故福善禍淫。固理也。理不能自爲。爲之者。鬼神也。此處恐或人之未達。故朱子姑應之曰。是也。或曰。然則鬼神。亦有所喜怒愛惡。必如人之有情耶。曰。鬼神與人。其理一也。故人之喜怒處。鬼神亦喜怒。人之愛惡處。鬼神亦愛惡。人之心。卽鬼神之心。鬼神之情。卽人之情。但人著而鬼神微。人顯而鬼神隱。惟有著微隱顯之分。其情意豈有不同也。故古之至誠者。爲徒於鬼神。與之合其吉凶。先生曰。子之論然。
問祭祀之說。先賢論之詳矣。終有所未瑩處。盖祭祀者。以己之精神。聚彼之精神。然後孫之祭先祖。後賢之祭先聖。其歿已久。其氣已散。更有甚來格者。後孫後賢之於先祖先聖。自有當報之理。以此理求之。則便有此氣也否。先生曰。末段以此理求之云者。似見得大意。盖天地萬物。本吾一體。今有感於邪魔者。一念專一。亦能有感。況正當道理乎。
問或曰。魂魄二者。有則俱有。無則俱無。葬而返也。宜乎魂魄俱返。而獨返魂。何也。盖魂是氣。魄屬質。屬於質者。形質在彼。必無歸來之理。氣是飄揚無定。宜有返還之道。故獨返魂耶。曰。返魂則返魄在其中。魂在於此。魄亦在此。闕一則無物。故於祭焚香以求魂。酹沙以求魄。合鬼神以享之。或曰。神是陽之伸。鬼是陰之歸。人死則是鬼也。題主宜曰鬼主而稱神主。何也。曰神是自無而有者。鬼是自有而無者。人死則鬼。是自有而無。祭而享之。是無中求有。盖鬼中亦有陰陽生死道理。感應來格。是亦陽之伸而生底理也。先生曰。魂魄之說。問者其言大槪近之。求魄之云。見於何經。吾寡陋未之見。下段所言。近之。○魂魄說。曩書所云。是平生誤執。而書發後忽自疑。其於魄太恝。就考書傳。則其與已見相左處非一。而朱先生。則不啻重言復言。此與六經何別。反而思之。則魂魄雖是二物。而必相依而後靈。故凡言神者。皆合魂魄而言者也。離則散而不靈矣。此是一件大事。而向來疏脱若此。乃欲開口說天下之理。可謂不量力矣。可愧。
問程子以聖人非不知命。然于人事。不得不盡謂。爲未是者。何也。先生曰。如此說。則天命人事。判然二物。故曰未是。然此處極難知。當深思也。
問或曰。伊川曰。孔子旣知桓魋不能害己。又却微服過宋。舜旣見象之將殺己。而象憂亦憂。象喜亦喜。國祚長短。自有命數。人君何用汲汲求治。禹稷救飢溺。過門不入。非不知飢溺而死自有命。而救之如此其急。何故如此。須思量到道竝行不相悖處。可也。聖人旣知有命。而又爲之如此。其義何也。曰。程子所言此等之命。以氣分言之。聖賢之盡其道。盡其性分上事也。或曰。然則天命自天命。人事自人事。程子以聖人非不知命。然于人事。不得不盡。爲未是者。何也。曰。或有天命如此。而聖賢順而行之者。或有聖賢盡道。而天命感而應之者。天命人事。常合一而無間也。安有天命如彼自運於上。人事如此謾行於下之理也。固知盛衰興亡。皆有定分。聖人求盡其性。而不委之於命。故朱子亦曰。若曰已知天命之如彼。而姑盡其事之如此。則是乃天命人事。判然二物。先生曰。吉凶成敗。固有定命。而干我何事。己修已分事。日不暇給。奚暇念到天命。天地不能相爲謀人。安能爲天謀。況命是藏頭物事。巧曆之所不能預度。而性分實理。昭著於心靈。引彼藏頭之吉凶。欺我昭著之心靈。可乎。是以事到論義。事過方論命。論命於事過之前。大亂之道。盛論大槪則是。而主意常欲合天人而一之。故終涉支蔓苟且。
問詩書言天人之際甚多。如天道福善禍淫。天何有情意。而必福善禍淫。先生曰。理之自然者。謂之天。
問自一至萬。所謂數也。是根於理。而作於氣。著於事物之間。具此數者。理也。行此數者。氣也。體此數者。物也。盡此數者。聖人也。先生曰。盡其數者聖人盡字。未易領會。盡知耶。盡行耶。聖人之聰明睿智。固能盡知。而但恐非所以語聖人。若曰盡行。則吉凶悔吝。豈皆身親經歷耶。
問人之生也。只是得於氣化之日。初無精神寓於太虛之中。及其死也。與氣俱消。更無形象留於沖漠之內。然則此身。只是天地間萬物中一箇物。而共公屈伸聚散者。有何所謂我也。旣無所謂我。則一切富貴貧賤。榮辱窮達。安樂憂戚。壽夭死生。更何有於我也。初無間於我。我亦無預於其間。然則天下更有何事。但順吾性而已。先生曰。我之爲言。本是對人而名。對立之意勝。則必至於循私滅公。故古人以平物我。爲見道之大端。今此所論。不可謂無此理。然推之太過。恐歸於太冷淡。轉入莊釋去。吾性亦何所安頓。須知對人之我。不可有也。立命之我。亦不可無也。
問向日承教。有脫灑之說。如何是脫灑。先生曰。凡言辭。各有意思所從起處。脫灑之云。不知曩時緣何提起。今不可追憶矣。姑就二字本旨言之。脫灑者。汩没之反也。着手脚超然。外物自然惹絆不得。則脫灑也。已身雜於物累之之中。日與之廝殺。雖僅能保其疆土。心與力俱疲矣。此未免汩没。脫灑豈非所願欲。而致此脫灑。必有本矣。惟理明義精。洞見大原。兼以持守純固然後。實踐是境。非希望造作之所可得也。然則言脫灑。不如言窮理存誠。曩時何爲而有此提起也。盖一步之行。未有不眼先於足者。今吾足雖未到此境。眼能先知有此境。則亦足胸次開豁。地步展拓。鄙意當時或出於此耶。若或心中留着脫灑二字。如佛者看話頭樣。則吾恐下梢所得。乃疏闊而非脫灑。請以是爲答。
問器亦道。道亦器。日用之間。居處恭。執事敬。足容重。手容恭。便是對越在天。先生曰。是。
問或曰。涵養是靜時工夫。曰。不拘動時靜時。常游泳於天理之中。奉順而不遺之謂也。故朱子曰。動靜皆有涵養。先生曰。涵養通貫動靜。省察單在方動。
問形體者。天理之盛載也。言語者。天理之發出也。故容貌必欲正。言辭必欲厲。先生曰。容貌辭氣。一身之體用。此而不謹。則天理無流行處。
問臨事須審其義之所在。而一循於理。無一毫用意爲之。先生曰。精義最難。人固有緣情立義。自以爲行天下之達道者。
問言語差錯。知不分明。心不安定之致也。故言語差錯者。臨事必差錯。先生曰。亦有說時不錯。而做時錯者。
問上不連致知。知行之分。下不連正心。何也。先生曰。不連於致知章。固然不接正心。盖正心。修齊之總領關鍵也。
問先惡惡而後好好。能惡惡而好善得遂否。先生曰。與鄙見無異同。
問西山眞氏。解張子所謂性者萬物之一原。而曰凡人物之性。皆自此流出。如百川之同一源。此言似未然。張子之言性字。貼在一原字上。物雖萬而性則一之謂也。直指統體言之。眞氏之言性字。歸宿百川字上。萬物之性同出一原之謂也。下落各具處也。先生曰。見得精密。更與明眼訂之。
問愼終追遠。南軒解以凡事如是。所以養德者厚矣。朱子辨之曰。下一養字。則是所以爲此者。乃欲以養德。而其意不專於愼終追遠矣。曾子之意。專在愼追上。而張氏之解。重在養德上。故云爾歟。先生曰。愼終追遠。非以養德。如曰言語必信。非以正行。
問朱子曰。聖人無怒。可疑。先生曰。聖人無怒。恐非朱子語。
問呂德昭問程子不取鮮于侁顏子樂道之說曰。恐是以道爲樂。與道爲二物。朱子答曰。說他不是。又未可爲十分不是。只是他語拙說得來頭撞。公更添說與道爲二物。愈不好。黃直卿又問。竊恐伊川之說。謂顔子與道爲一。若以道爲可樂。則二矣。朱子答曰。大槪得之。二子問同而答異。何也。先生曰。呂德昭云云。語非不是。但鮮于侁本語之外。加添得不好。故言其不當如是。
問用行舍藏。謝氏曰。聖人於行藏之間。無意無必。其行非貪位。其藏非獨善。始可謂眞知物我之分。楊氏曰。樂則行之。憂則違之。孔顏之所同。使天下文明孔子而已。呂氏曰。用之行。舍之藏。孔顔所同。可以仕則仕。止則止。孔子所獨。朱子曰。謝氏知物我之分。恐非所以語聖人。呂楊分別孔顔不同處。亦有此意。此意何意。先生曰。聖人無迹。謝氏别尋一個形跡來。所謂呂楊此意。謂是耶。
問子在川上云云。先儒以逝字。非指水。斯字方指水。竊以爲逝。指水之流而言。如斯。指不舍晝夜而言。盖見水流。而歎其流也不舍夫。而道體流水之妙。自見於言外。如先儒之言。則意味有所未盡。先生曰。逝者之論甚新。而曰者曰如。終有包含衆逝意味。更加玩味。如何。
問金致熙曰。集註與道爲體。頗有與道爲二之嫌。曰。程子之意。盖物生水流。無非道之所爲。故上句直曰此道體也。然物生水流。非道體而直曰道體。則有道器無分之嫌。故又解之曰。與道爲體。道器有上下之分。而只ㅇ是一形。則此與道爲體之意。先生曰。答說大意。似然。
問顔淵死。門人厚葬。蓋不幸早卒。爲其門人者。欲其無使土親膚。厚葬固人情。而夫子以爲不可。何也。蓋天不道理。只有一箇中而已。過猶不及。且以物尊之。孰如尊之以道。違道以尊。知道之人所不爲也。先生曰。然。
問死生有命。張子曰。論死生。則曰有命。以言其氣也。語富貴。則曰在天。以言其理也。謝氏曰。命自其所稟言。天自其所遇言。此皆何謂也。先生曰。命與天。固無分別。而曰有命。則是自上降下之辭。曰。在天。則是自流溯源之辭。故可分屬。然而無理。豈有氣也。其實一而已。自上降下。故曰所稟。自流溯源。故曰所遇。
問莫我知也夫。伊川曰。王通曰。知命者。不怨天。自知者。不尤人。王通豈知所謂命者哉。至如釋氏有因緣報應之說。要皆不知命者也。王氏之言。似無病。而程子云爾。何也。因緣報應。又何謂也。先生曰。知命者。不怨天。以下文自知云云觀之。蓋謂命乃吾身所賦。而反歸怨於蒼蒼。則不可也。其言未嘗不好。而若言命字本旨。則失之矣。程子之言謂此耶。因緣報應。言此生之吉凶禍福。皆前生結因緣而收報應於後生者也。
問大德不踰閑。明道曰。出入可也。出須是同歸云。同歸者。何謂也。先生曰。出者中有背馳者。有同趨向者。所謂同歸。言其雖不由軌轍。而亦非背馳者耶。
問權然後知輕重。止王請度之。朱子曰。此求仁之方。精義之本。蓋心之官則思。思則得之。思卽求仁之方。精義之本。所謂度。卽思也。先生曰。思字於精義爲襯。求仁二字。一念反求。已躍如。
問四端不言信云云。在孟子是氣。何謂也。先生曰。元亨利貞。不言信。蓋實有是理。則這便是信也。四端不言信。蓋實有是發。則這便是信也。發者氣也。故曰在孟子是氣。伊川之意。如是耶。
問自齊葬魯。先生曰。孟子去齊之前。恐是挈家在齊。故歸葬反齊。反齊二字。豈可以出仕看乎。
問無爲其所不爲。守之於爲之事也。無欲其所不欲。誠之於思之事也否。先生曰。然。
問朱子中庸說曰。率性之道。大化流行。各有條貫也。答林擇之書曰。率性之道。人性之當然也。若呂氏直以率性爲循性而行。則宜乎以中爲道之所由出也。答陳才卿書曰。道只在性之流行分別處。非是人率性而爲此道也。以此觀之。則率性之道。是理之自然流行。各有條貫。非謂人之循性而行。先生曰。率性。如曰無所差失於性。若下自然流行等語。則恐涉四端地界。非道字本旨。
問或曰。朱子答林擇之書曰。未發之中。以全體而言。時中之中。以當然而言。要皆指其本然而言也。時中之中。以人事言。而何謂本然也。曰。吾嘗以爲未發之中。卽劉子所謂天地之中。時中之中。卽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。時中雖指人事而言。中則固本然也。蓋有本然之中。故人隨時而中也。先生曰。答說是。
問金致熙曰。至靜之中。無所偏倚。至靜卽未發時。有何偏倚不偏倚之可言。曰。喜怒哀樂未發。謂之中。旣有中之可言。則豈無無偏倚之可言乎。先生曰。無所偏倚。方成眞未發。若如水之波浪雖息。而餘濁未淨。未發不可謂之中矣。
問姶封之君。不臣諸父昆弟。封君之子。不臣諸父。而臣昆弟。然則封君之孫。臣諸父歟。先生曰。然。
問鄭載圭謂禮器曰。君在阼。夫人在房。【註西房】此陰陽之分。夫婦之位。當如家禮祠堂敍立之儀。而中庸序昭穆註。左昭右穆。子孫亦以爲序。群昭群穆咸在。而不失其倫。父子分昭穆。而位于東西。則夫人位于何處。時未能有對。近考祭統註。昭穆以神爲主。故人於廟中仍稱之。因此思之。則其謂群昭群穆咸在者。非昭東穆西。倣神位止。謂父昭子穆。群子群孫咸在也。此昭穆字。只是行列之稱。禘嘗之禮。所以仁昭穆。亦爲仁父子也。蓋入在廟中。故借而稱之。未知如何。先生曰。所論是。
問學困利勉。工夫也。知之行之。以功效言之否。先生曰。是。
問敦厚崇禮。所謂忠信之人。可以學禮者耶。先生曰。然。
問咸有一德。善無常主。協于克一。善無常主。義有萬殊也。協于克一。理本一之謂耶。先生曰。善無常主。如曰中無定體。協于克一。如曰一以貫之。
問輯瑞頒瑞。程子謂與天下正始。當時舜雖攝政。天下乃堯之天下。諸侯皆堯之諸侯也。舜安敢與天下正始。恐是詢察諸侯之例禮也。先生曰。雖非卽位之初。乃是攝政之一初。故其說如是。所論大體則然。
問庶民惟星。謂民之麗土。猶星之麗天。星有好風雨。謂民各有所好也。日月之行。有冬夏。君臣之職。本有常道也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。蓋從得其道。則風雨也休。從失其道。則風雨也咎。月卿士。衆星庶民象。故曰月之從星。驗卿士。星之風雨。驗庶民之情。而民情隱而難知。天象著而易見。故言也。先生曰。推得似仔細。
問易有太極。朱子曰。自太極而分兩儀。則太極固太極。兩儀固兩儀。自兩儀而分四象。則兩儀反爲太極。四象又爲兩儀。此何謂。先生曰。兩儀反爲太極。理無多寡故云。
問定公十五年夏五月壬申。公薨。秋七月壬申。姒氏卒。九月丁巳葬定公。雨不克葬。戊午日下昃。乃克葬。辛巳葬定姒。胡傳引葬先輕而後重之說以譏之。然則父喪後數月。母卒。葬當先母耶。先生曰。先輕之說。蓋指先後不爭。多可以變通者而言。豈過期不葬。延待後葬之葬耶。
問孔子曰。父母之仇。不與共天下。遇諸市朝。不返兵而鬪。兄弟之仇。仕不與共國。銜君之命而使。雖遇之不鬪。若銜君命。則雖父母之仇。難與之鬪。先生曰。然。
問曾子問。君薨而世子生。祝告之曰。某之子生三月。祝告之曰。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。子拜稽顙踊云云。又曰。如巳葬而世子生。大祝告于禰。三月仍名于禰云。若衆子生。則其禮如何。先生曰。必以世子爲言。則衆子生。其禮必殺。或當告之而已耶。未敢質言。
問喪大記。以衰抱之。若已葬而宗子生。則祝亦衰抱告之。自此日期而小祥。再期而大祥。除之否。先生曰。小大祥之說。似然。
問有君喪服於身註。若親喪小祥後。遭君服。則他時君服除後。行大祥祭也。夫以所在致死之義觀之。君父初無輕重。而先遭父喪。則是致死於父之日。而後遭君喪。猶不敢服父。何也。先生曰。服有所壓。致死。非所言也。
問賤幼不誄貴長。先輩於師長有挽。何也。先生曰。挽誄不同。
問喪服小記。庶子不祭祖者。明其宗也。註此據適士二廟祭禰及祖。今兄弟二人。一適一庶。而俱爲適士。其適子之爲適士者。固祭祖及禰。其庶子雖適士。止得立禰廟。然則俱爲適士。豈各立禰廟耶。先生曰。一適一庶。俱爲適士者。或是兩家。故如是耶。若是一家人。則禰廟無雙立之理。更詳本註。如何。
問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父稅服。已則否。註謂生於他國。而祖父母諸父昆弟在本國。已不及識之。今聞其死。日月已過。父則追服。己則不服。註說恐未備。所謂生不及者。似是己未生之前。祖父母諸父皆已死。而今始聞喪。死生異代不相及之謂。非不及識之而已也。先生曰。子之言。是經文本意。
問父母之喪偕。先葬者。不虞祔。待後事畢。先虞父後虞母。卒哭當待葬。而虞祭似不待後事畢。先生曰。此虞似非返魂之虞。
問大傅。自仁率親。等而上之至于祖。名日輕。自義率祖。順而下之至于禰。名曰重。重謂祖重耶。禰重耶。詁用義循祖。循而下之至于禰。其義漸輕。祖則義重。故名曰重。此則謂祖重也。註自義率祖。順而下之以至于禰。名曰重。以其仁有所隆也。此則謂禰重。先生曰。輕重皆以祖言。
問樂記。明則有禮樂。幽則有鬼神。何謂耶。先生曰。禮樂以人道言。禮屬陰。樂屬陽。可見。故曰明。鬼神以天道言。鬼是陰。神是陽。不可見。故曰幽。
問喪大記。左衽結絞不紐。註生向右。左手解帶。便也。註說沒意味。恐生陽也。左是陽。故以左加右而右衽也。死陰也。右是陰。故以右尙左而左衽也。先生曰。左右衽。所論似有理。而註說未之言。或疏脫耶。
問循與徇。先生曰。徇有惟人是從之意。與循字不同。
問申鍾求曰。太極圖上一圈。所以動而陽。靜而陰之本體。黑爲陰。白爲陽。外黑內白。陰含陽之義耶。曰。上一圈。卽所謂太極。蓋此圖。闡理氣之本原。發造化之微妙。故將排寫形而下之陰陽圈。先揭形而上底太極圈。以示有理而後有氣。而爲萬化之樞紐。品彙之根柢。理本無捉摸處。特下一圈子。以形無形。示無中有。虛中實之理。所以爲動而陽。靜而陰之本體也。陰含陽之義。恐不可卽此而言之。宋時一曰。上圈不雜者也。中圈不離者也。曰。謂上以示不雜之義。中以示不離之義。則可。如盛論。則上中圈。分爲二層。不離雜。分爲二極。恐不可。先生曰。子之論。甚精。
問精粗本末無二致。何謂也。灑掃應對。是其然。必有所以然。其然者。粗也末也。所以然。精也本也。先生曰。似然。
問萬物各具一太極。統體一太極。以爲統體。合萬物言。各具。分萬物言。今又思之。統體就天地分上言。各具就萬物分上言。此理在天地。則曰統體。在萬物。則曰各具。此與前說毫釐。而旨意殊異。先生曰。太極說話。大抵位虛理實四字。足以盡之。圖中上面一圈。至萬物化生圈。曷嘗實有稱等確定也。此所謂位虛也。五層圈子。皆一味白淡淡底。圓足無欠缺底。此所謂理實也。看得虛實各有着落。而兩不相妨。方是善看。盛語上一節。欲以實理。埋却虛位。下一節。欲以虛位。掩却實理。似欠實見。蓋統體各具四字。本自虛位邊說來者也。
問上天之載。無聲無臭。其體則謂之易。其理則謂之道。其用則謂之神。其體其理。何謂也。先生曰。體似以全體言也。理似以條理言也。
問伊川日。有陰便有陽。有陽便有陰。有一便有二。才有一二。便有一二之間便是三。已往更無窮。老子言三生萬物。此是生生之謂易。理自然如此。一二是陰陽也。三便是萬物。而才有陰陽。便生萬物之謂歟。先生曰。以已往更無窮之語觀之。三是萬物之母。而非謂三便萬物也。
問伊川所謂一二之間。邵子所謂一動一靜之間。間字同不同。先生曰。程子所謂一二之間。與邵子一動一靜之間。不同。此以氣言也。
問涵養須用敬。進學在致知。朱子曰。涵養本原。思索義理。須用齊頭做。方得互相發。程子下須字在字。便是要齊頭着力。須在二字。何謂齊頭着力。先生曰。須字在字云云。可見古人看文字。咀嚼出意味處。蓋此兩字。皆在主一邊。不遺一邊之意故也。愚見如此。未知然否。以在字言之。說在明明德時。已含在新民之意。說某在斯時。已知更有某在斯在下面。
問龜山曰。讀西銘。知爲學大方。因以思之。學是復性。性所具仁義。仁理一也。理一中自然底分殊義也。理一則天地萬物一體。分殊則親疏貴賤有差等。天地間只有此道理。人之所得於天。亦此道理而已。故知其理一。知其分殊。一而有分。此爲學大方。及其至。則盡吾性。參天地。西銘所言。是這意。而龜山之言。似此否。先生曰。所論然。
問太極自是涵動靜之理。却不可以動靜。分體用。却不可與動靜分體用之謂耶。先生曰。見得是。
問李孝述問。四時五氣之布。五氣之生。定於其初。恐非至此而序生。但氣之流布。其序必如此而後可。若爾則那一氣之行也。彼四氣。定在何處。先生曰。理無增減。故可謂一時都具。氣有形迹。故未免流行有漸。孝述之言。雖未明暢。其意思。則未見其不然矣。然而其間。亦有一時竝行者。夏是長養之節。而半夏生則春也。麥秋至則秋也。夏枯死則冬也。
問聲色臭味之欲。發於氣。所謂人心。仁義禮智之理。根於性。所謂道心。此語下一半。當改之曰。惻隱羞惡之情。根於性。所謂道心。則如何。先生曰。西山所謂仁義禮智。卽指四端而言。古人文字。當活着服目。豈可拘拘若是。
問吳臨川曰。太極本無體用之分。其流行變化者。皆氣機之闔闢。有動時。有靜時。當其靜也。太極在其中。以其靜也。因以爲太極之體。及其動也。太極亦在其中。以其動也。因以爲太極之用。太極之沖漠無睽。聲臭泯然者。無時而不然。不以動靜而有間。亦何體用之分哉。竊謂氣機之闔闢動靜。其所以然則太極也。若如吳氏之論。則太極只一塊儱侗物。先生曰。子之論。卽吾意。
問五代六代祖喪。亦當造主耶。曰。當造主奉之靈筵。三月後撤靈筵則埋之。以其無奉安之地也。先生曰。雖五代六代孫。生時旣奉養。則當終其身奉祀。何可三月埋主。
問曾以五六世祖喪。撤靈埋主。仰稟。答云云。但言遷埋之非。不言奉安之地。鄭載圭云。生旣奉養。死常主喪而奉祀。豈有不終其身之理。但不無曲折之難安。蓋五世祖生時。高祖以下神主。宜在祔位。而及其喪畢。改題五世以上當遷。以下當躋正位。則五世祖無奉安之位。當奉別室。而此亦可疑。五世祖未入廟。而高祖遽躋正位。其於父傳子承。世次迭遷之義。不有欠闕耶。又以爲後之嫡孫。奉傳重之正祖。而不於正廟。徑遷之別室。亦所未安。如何爲當。先生曰。祥後入廟。而及吉祭之期。以五世同廟。典禮有碍之意告由。而遷于別室。何持難之有。
問承重庶子神主。入於本宗祠堂。答當人而不可倂坐。增解蓋庶子旣承重。便成嫡子。竝坐何嫌。先生曰。所論是。
問宗孫有五代六代。次孫有曾玄。則於是祖之喪。誰爲主。曰。雖次孫。旣有曾玄孫。則恐當主之。先生曰。此事不可句斷。五代六代孫。生時旣奉養。則安可以一朝身歿。而卒然易主也。
問凡喪告廟。當先於訃親戚。先生曰。先告家廟。
問絞帶順目反目。先生曰。三重四股。反目爲是。
問通典。父死未殯而祖死。服祖以周。蓋不忍死其父。然父已死而祖死。豈可不制祖服斬衰耶。先生曰。服祖以周四字。以備禮家之一說。非欲必此遵行。
問子在父喪亡。而適孫承重之說。前此已累度問辨。而今觀增解諸說。則所論不一。愚伏則曰。以始制爲斷。通典服周者得之。李氏則曰。父已承父重而死。豈宜奪其父已承之重。縮一代而越承祖重耶。又曰。今以孝服陳靈。是父尙持服。子又持重。則一喪之中。父子共之。竊詳愚伏所引通與。不可謂無据。未知其得中。至若服以始斷云云。凡服之不以始斷者不一。且服朞。本服也。制斬。代父服也。意義不同。李氏奪重縮代越承之說。殆涉駭然。夫其父雖承父重。未終事而亡。故代父承重。順其孝心。豈謂奪重縮代越承也。亡者孝服。陳於靈床。旣葬而撤。其子承重。亦於父葬後。則豈可謂父子共主。宋敏求則曰。因父葬。再制斬衰。尤庵先生則曰。祖未葬而遭父喪者。代服之節。當因祖葬制斬衰。祖已葬父死。服祖斬。當在成父服之日。遂庵則曰。只得繼父服其餘月。因父葬再制斬。因祖葬制祖斬。持服繼父服餘日。固至當定論。李氏又謂。嫡孫承重而亡。其妻立後。則爲後者。只服所後。不當代服曾祖斬。小子之意。則此亦於所後父葬。受曾祖斬。先生曰。祖喪巳成服而父亡。此是禮經闕文。今不敢質言古禮之如何。而喪不可無主。註疏中有父有篤疾。長子代父執喪之說。篤疾猶然。況於父喪乎。似當以此傍照行之。則宋敏求已是的當。更有何議論乎。若其受服之日限。則曩有人遭此者。其時淺見以爲祖喪業已成服。而父喪未葬。更受他服。亦渉不遑。故先輕葬畢後。啓殯受服。似穏云矣。其後見諸家之說不一。要在當人擇而行之。若其近世禮家越承之論。眞是可駭。承重自承重。重服自重服。孫之代父執喪。豈待受重而始行乎。此禮家狃於陋俗。認承重爲重服之名故然耳。勿論。可也。餘日之論似當。受曾祖斬亦然。不如是。何以表爲後之義也。李氏爲承重。二字所縛。脫出一歩不得。多少可悶。
問先儒曰。喪中死者。喪服陳於靈床。旣葬撤去。服已盡於葬前者。亦旣葬而撤耶。先生曰。然。
問或曰。子在父喪而亡。嫡孫服重。必待父葬。則不無間斷之嫌耶。曰。此至情精義所當深思處。未葬前焉得死其親旣葬則返而亡焉。於是不得已代父服重也。間斷之嫌。何有於此。先生曰。子之論是。
問祖喪中嫡孫死。次孫承重當否。南溪曰。長孫有弟當服祖三年。待異日立嫡爲料。則當如徐邈所謂以本服攝主。旣除素服臨祭。以終三年。可也。豈可以閏於其間。服祖三年。李氏曰。嫡孫亡無妻。不得立後。次孫不得已告廟承重。似當以通典所論練後來後於伯父。彼喪雖殺。我重自始。更制遠月云者。可以傍照而處之。以告廟始制之日計之。滿二十五月之期。此言恐亦未然。通典云云。或以伯父無後。初無服重者。其姪來繼者言。故謂我重自始耶。若祖父之喪。適孫居喪未竟而亡。次孫承重。則似當繼服嫡孫未竟之餘月。先生曰。爲後。則當服遠月。
問祔葬先麓。徧告各位耶。只告最尊位耶。先生曰。諸位墳墓。密近新葬地。則似當各告。稍遠則只告最尊位。
問嘗稟主五代六代祖喪。當服齊衰三月。陶庵亦云。而鄭載圭云。此當更思。蓋逮事五代祖。當服齊衰三月。見語類。竊以爲主其喪者。當服三年。蓋因朱子說而得之。齊衰三月。本高祖正服。而逮事五代祖亦同者。以其正尊之服。無可以復殺言逮事。則是必有父祖主喪而已。但以逮事而服。今爲其後主其喪。而同諸孫之逮事而已。則恐非朱子之意。以齊衰三月之親。而爲後則服三年。恐無間於高祖。未知如何。先生曰。此說甚當。
問繼禰之長子。亦爲之斬衰三年耶。先生曰。先儒之論。亦有如此者。
問爲人後。不爲長子斬。然乎。曰。承人之嫡統。而將傳重於其子。則已之爲後。似不當論也。先生曰。吾意以或說爲主。而我東禮家之論。多不然。
問禮疏云。三年内母卒。仍服朞。小子之意。則父喪葬後。母卒當三年也。先生曰。父卒爲母三年。恐不必待葬後。蓋經文但曰。父卒則爲母。疏家乃有待三年之說。恐難必從。
問祥後禫前立後。似當追服三年。先生曰。服本期年。加隆之服。止於再期。二祥則再期已過。更制重服。於禮似過。
問女子成婚後。不卽歸夫家。遭父母喪。亦降耶。先生曰。當降服。
問嫁返在室。爲父斬衰。則無夫與子者云耶。先生曰。爲夫所出者。
問庶子爲父後者。爲其母緦。而無他子爲母後。則撤靈於服盡之日。於初朞直行忌祀耶。先生曰。然。
問喪服傳爲父後者。爲出母無服。疏爲父後。謂父沒承重。疏說可疑。未承重。爲出母有服耶。先生曰。疏說不可。
問爲人後者。於本生父在母喪。期而除服後。緇笠緇帶。在家兄弟無別耶。先生曰。皆心喪。恐無分別。
問母出。則爲繼母之父母姊妹小功。註母死。則爲母黨服。不爲繼母之黨服云。繼母之子。亦服其母之黨。而於前母之黨無服耶。先生曰。然。
問遂庵曰。殤服以上中下。各降一等。故殤者於長者。亦以三等各降一等。如八歳童子於叔父喪。當服五月。南溪曰。禮有上下尊卑之體。尊者雖以童子減服。卑者不敢以童子減長者之服。恐當從南溪。先生曰。當從南溪議。
問或日。自啓至虞。節節有祝。而下棺無祝。今觀先儒說。下棺有祝曰。今遷柩就壙敢告。曰。家禮無下棺祝。蓋有深意。非所以處大變也。此蓋朱子所不忍言也。沙翁所不敢補也。先生曰。子之論。似然。
問增解父母偕喪。雖一日母先亡。則服母以期。題主須題以顯妣。而旁註云子某攝祀。又與父與祖父母偕喪。祖父母題以祖考妣。而旁註稱孫某攝祀。喪畢改以孝孫云。此論恐不可。題以顯妣。子爲主也。題以祖考妣。孫爲主也。旁註直書孝子孝孫然後。言順理直。此雖出於不忍變在之意。聖人所謂三年無改者。恐不若是拘拘。先生曰。題主。非爲今日祭奠而題。乃昭穆繼序平生之計。孝字之題。烏得免乎。攝是非其主而權宜來助之稱。喪中之子。謂非其主則不可。且生子攝死父。禮有其文歟。恨吾寡陋而未之見也。若爲今日祭奠。則喪祭不稱孝。葬時孝子之題。亦未安矣。
問主婦以亡者之妻爲之。然祭亡弟小子攝事。與弟婦共事有嫌。舍其妻而以賤婦爲之。先生曰。攝主本是無主。而代主豈可尋主婦。
問雜記曰。當父母喪。除諸父昆弟之喪。服其除喪之服。卒事反喪服。通典賀循曰。雖有父母喪。爲期大功喪除。各服其除喪之服。據此則親喪中。除期大功者於行祀時。着吉服無疑。而沙溪曰。服其服入哭而祭時。不可着吉服。只着頭巾與布衣。愼齋曰。行之以深衣孝巾。南溪曰。白布笠白布網巾白布衣。只借白色衣冠。蓋此衣冠。旣非孝子之服。又非除喪之服。小子之意。從古禮。未祭前服其服。行祀時着吉。祭畢反服。未知如何。先生曰。白深衣白布衣。以至華盛之服。皆可名吉服。除服之吉服。必非華盛之服。況身在大故乎。然則深衣布衣。恐非可疑。
問凡服緦一時。小功二時。大功三時。三年後禫加一時。閏非正月。似不當筭。筭之可疑。先生曰。禫非加一時。禮中月而禫。王肅解作是月之中。今雖用從厚之禮。而朱子是王說。
問前後有喪。前喪禫。不可行於後喪中。沙尤諸先生。已有定論。而李鏡湖謂。親喪中。尙以吉服。除朞功之輕服。豈有不可暫服除禫之服。以行前喪禫也。李氏之說。似亦有理。先生曰。禫者。湛湛然平安之意。喪中豈可行禫祭。
問愼齋曰。吉祭不可攝。尤庵曰。祧遷。似非權代者所敢當。陶庵曰。一時權宜之人。改題遞遷。萬萬未安。愚見改題。非權攝者敢爲遞遷。乃長房事。似無不敢。先生曰。改題。遞遷。是一項事。不宜分而二之。但主後久未立。則應須不得已而有權宜之道。
問改葬返殯於家。固非有進無退之義。然尤翁之言曰。哀家旣還殯於家。則與几筵同處一室。竝設兩處几筵。未知如何云。據此則先賢亦有返家者。三年内改葬。上食饋奠。尤翁言。母寧舍几筵。而行於殯耶。同春言。竝設於靈筵及柩前。愚意似當單設於靈筵。而不敢臆斷。先生曰。返殯一節。有進無退。道其常也。處變豈可拘也。祭奠雖曰如此。以愚見則皆可疑。未葬前。未聞柩前別設。改殯日。豈有別般禮數也。然則棘人之言。乃吾意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