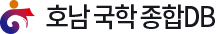- 국역/표점
- 표점
- 동오유고(東塢遺稿)
- 卷之四
- 江上箚錄【遺稿將梓。就箚錄中。拈出師席訓誨言行答問及他藏否之及於耳目。足以勵世者分爲四彙。編之卷後。其餘隨聞雜記。以備遺忘者。亦不爲無助於後輩。而稍涉繁冗。故淨寫以藏其家云。】
동오유고(東塢遺稿) / 卷之四
江上箚錄【遺稿將梓。就箚錄中。拈出師席訓誨言行答問及他藏否之及於耳目。足以勵世者分爲四彙。編之卷後。其餘隨聞雜記。以備遺忘者。亦不爲無助於後輩。而稍涉繁冗。故淨寫以藏其家云。】
余初名以溢。蓋惑於造名之說也。日先生問余名何以溢。爲器滿則溢。溢非嘉字。余以實對。先生哂曰。造命禍福之說。豈有是理。宜取平正字名之。余歉然而愧。幡然而悟。請名焉。先生曰。若從水邊。則洛河漢等字。皆可也。取洛字爲名。因問名以洛。旣聞命矣。字當何爲。先生曰。初字云何。曰士弘。先生曰。洛出書洪範作。代弘以洪。無妨乎。他日先生於人書牘中。見余字。因曰。士洪是子之字耶。有任士洪者奸人也。見之輒覺礙眼。初未之思也。因請改之。先生拈出敍九二字命之。蓋以禹敍九疇。應洛字之義也。余自後於術數之說。不之信焉。噫。先生敎術不一。每對人諄復剴切以義喩之。類如此。君子愛人以德。信哉。
稟於先生曰。小子柔有餘。而毅不足。請改名以毅。以爲顧名思義之資。先生曰。可也。士弘二字。亦合乎。
先生曰。子之齒幾何。對曰。三十有五。先生誦離騷經日月忽其不淹兮。春與秋其代序。又誦古詩請君莫惜金縷衣。請君須惜少年時。又曰。士弘乎。耳目非不聰明心地非不正也。年近四十。如無所成名。可不惜哉。此宜所警省處也。問書法。先生曰。程夫子與人書云。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。蓋言專攻乎此。則有不暇及他故也。又曰。學書者。日書百字。不如此。便不熟。是豈易言哉。但儒者書拙構。何傷乎。又曰。尤庵先生。初不藝於書。日謁愼獨齋。適有人印七書。請書題目。顧謂尤庵曰。君若善書。可代此勞。尤庵退以葛筆習書於庭畔石面。法旣就。謁愼齋。印冊尙在。請書題目。愼齋哂之。遂抽筆書之。筆法甚健古。愼齋許之。先生發此言。以手畫地。作揮灑樣。甚有筯力。若目覩焉。
余與晉錫侍先生。先生曰。爲男子處世。雖泰山崩於前。色不變。麋鹿興於左。目不瞬可以濟事。
先生曰。世間橫逆之來無限。纔聞逆耳之言。便塞胸臆。安能處事得宜哉。又曰。責人過。吾當先立於無過之地。然後。可矣。若自身先立於汚穢之中。而責人之不潔。可乎。蓋有爲而發也。
先生曰。敎兒若泰和家兒。則可敎也。長子子每受書退讀。有疑晦必發憤。少子子窮尋細究云。余曰。小子自兒少時數十年工夫。都歸虛事。先生曰何。對曰。但隨敎隨讀。無一分商量意思。旣長。强引思索。每欲細究。則未及解得。便覺煩鬧。先生然之。
先生曰。士弘乎。世間疑事。亦多般樣子。無疑問。得非少思量乎。對曰自知病根在裏許。而改之未能。敢問如何。則祛此病乎。先生曰。磨劒必以礪。非礪而望其鋒者。末矣。古人之書。其吾心之礪乎。
先生曰。人有思索而後有成。余對曰。思索亦屬於才也。曰。然。子見蘇君明乎。曰。未也。曰。斯人也有思量才。孶孶焉須臾不忘乎思量。吾見斯人也。不幸短命死矣。又曰。三嘉鄭生載圭。慧而多思量。其有望乎。
先生曰。士弘乎。敎與學相長。不其信乎。此雖小事。輤之爲載柩車。蓋因敎賢而詳乎。輤倉甸切。音倩廣韻載柩車。蓋禮雜記。諸侯之輤有裧。大夫以布。士以葦席。註輤載柩。將殯車飾也。殯謂之輤。葬謂之柳翣。玉篇或作倩。集韻通作𧚫。
先生問。業何書。未及對。先生曰。大凡看書。常須照顧後面。頃年鄭載圭問讀書法。吾答凡看文字。常須照顧後面。切忌貪前云。若閱眼忘了。如老人破寂樣。則末矣。
先生曰。國有大慶。慶科將設。有觀光意否。對曰。淡淡。先生曰。同慶之義。不可坐定。所欠者裹糧也。是夜未半。先生起坐曰。士弘乎來。凡科宦。孰不欲。雖至愚者欲之。至奸者欲之。能安分竢命者。其惟哲人乎。向也予言淡淡而吾言似謾沖起。心有所不安。故復告賢也。對曰。非安分竢命。自知所持者挾。不足以耀人眼目。必無可得之理。故意思從以淡淡。非本無欲也。豈敢曰安分也。先生曰。自知其不足。不妄生意思。便是安分。惟賢所安。
先生以朱夫子答孫敬甫書示之。卽論山家說也。蓋其議論。參酌節中。過者抑之。不及者引之。使人觀之。足以爲懲爲法。
先生問曰。子多夢乎。對曰。不多。或有之而不能記。先生曰。心地恬淡。自然少夢也。
先生曰。士弘乎來。進就底人多思想。凡進就之工。自思念中出來。朱夫子感興詩云。玄思徹萬微之句。亦可見其思想也。余自少時。性多思想。或終夜不能眠。食不甘味。反覺苦惱。乃以强制己十年矣。又曰。吾之發此言。非他。子有志於學有年。而思想不多故也。
先生曰。人之有文名。甚不幸。余對曰。自古英雄烈士大人君子。豈有不文而聞人者乎。先生曰。爲士者。博古通今。免無識則可矣。文名則不可。子聞諸葛孔明范文正公有文名乎。然而下筆便成珠玉。如此方可。昔劉摯云。一號文人。餘不足觀。許衡謂姚燧曰。非其人而與之。罪也。皆爲此也。吾於人無所恩怨。而每以文字多見負於人。若非此名。豈至於此。先生曰。士弘乎。試問太極之理。立於陰陽未行之前。陰陽之氣。行於太極已立之後。此說何如。余起對。小子未有宿講於此。雖不敢倉卒答述。而以臆見料度。則太極中已自有陰陽。而陰陽亦不離於太極。則太極與陰陽。恐不可以先後論也。若如此說。則是今日有太極。明日生兩儀。又明日生四象。而乾坤或幾乎息矣。似不成說。未知何如。先生曰。子之言雖未瑩。似近之。因曰。綾州文生年纔十八。以其所記來示。乃一幅長書也。輒看第一起頭有此語。余不復掛眼。責而歸之。【已上十七條。記先生敎訓及答述。】
丙寅九月。洋夷犯江都。人情汹汹。余時陪先生。李南坡孝一氏亦在座。時前兵使李承淵。奉命南下。號召義士。使人請檄文於先生。是夜夜將曙。先生曰。起起孝一乎。余夢與人過靑嚴驛。其人落後。且呼且行。忽有一人牽黑獸而至。視之脅折而肺肝露。怪問曰。何獸也。曰。羊也。夢也不偶。子其占之。南坡曰。洋其滅乎。洋登陸失水則羊也。脅折而肺肝見。羊其死乎。先生曰。然。吾亦以爲然也。洋之所爲。如見其肺肝。然彼必不能肆其伎倆乎。不幾日。鼎足一捷。江都復淸。噫。自洋夷之侵擾沿海。先生寢食不自安。對人輒告以洋夷之凶醜。且有爲文召同義之擧。聞召募使南下而止。以其文小改其末段。應召募使之請。蓋其忠義所發。滅洋之兆。已驗於夢寐也。
先生曰。秋收橡子讀書者。世或有之。蓋歎時人食粟而不能讀書也。
先生敎人書法曰。以指書之。不以臂。以毫體畫之。不以毫端。此所以不成也。先生則操筆。必擧肱不貼地。
戊辰冬至夜。先生曰。起起士弘乎。新陽已回。吾年已七十二矣。少孔子一年。多朱子一年。因問子之親年幾何。對曰。六十八歲矣。氣力何如。對曰。自來康健矣。年來衰敗特甚。先生曰。七十老人矣。安得不然。親年益邵。爲子者誠爲可喜。而年迫朝暮。寧不可懼乎。
先生敎訓諄切。無所不至。見爲子弟者。則勸以孝弟。爲學業者。則勸以文學。爲産業者。則勸以作業。見年少輩。則必戒以酒色。常曰。雖非現然爲祟。已自津液涸渴。精神耗損。受傷多矣。纔被他所祟。浸成難救之症也。
先生曰。古人於無可奈何處。必曰命。今人於禍福。必曰山驗地理。非曰無有。而先有天理然後。地理隨之。若掘親骸。累年不葬。妄求福地。以覬其驗。則天理已違。安有地理。蓋時有如此者。故發之也。
先生曰。凡父母之喪三年後。緬禮尸柩。當奉于其家。如初喪時。朝夕哭上食。但設虛位可也。今人拘於俗忌。或尸柩過門不入。而殯于山野。經宿乃葬。其可乎。
先生曰。大舜好察邇言。顔子以能問於不能。以多問於寡。諸葛孔明曰。諸有忠慮於國者。但勤攻吾之闕。則事可定。賊可死。功可蹻足而待矣。自聖人以下。常有自不足底意。然後方寡過。又曰。人常自以爲不足。則萬善從此生矣。自足則知日蹙矣。
先生曰。吾聞諸泰和。素灘有金氏兄弟。光山人也。家貧分居。兄之田未糞。不敢先己之田。耕耘收穫。亦如之。兄有田而欲賣之。聞之賣己田而止其兄。凡事繫其兄者。無不盡心努力。此可謂天性也已矣。
先生曰。余小科時。監試官柳楚山致明。會試官洪相奭周也。且曰。洪相爲雜科試官。副試官將有所私。而洪秉公不敢犯手。思百端不已。直告于洪。洪不答。小頃謂曰。同爲試官。我獨賢勞乎。因推委之。副試官遂容其私。洪不犯自家手。時人謂之難。蓋有爲而發也。
先生召其孫宇萬曰。祖先文字。留子孫家。以爲子孫觀。未爲不可。切不可刊行于世。辱先大矣。何者。今俗有祖先文字。則刊板爲多帙。無論知不知家。皆送之。受以爲壁塗者。吾嘗目焉。秤重而送紙房。作還紙者。吾亦耳焉。此皆非君子之所爲。而槪不如留子孫篋笥而自珍之爲愈也。
丙子正月二十五日。先生遭子喪。着平凉子。布纓衣中單絞帶。二十七日小斂。先生曰。得無速乎。吾聞古人有四日復生者矣。一日扶杖登古城峯。營掩竁也。顧謂宇萬曰。吾於無遑未及矣。乃以北布製中單耶。此乃南中人之華服也。當喪者。豈可服乎。如有生綿一端。則更製可也。
奇正言陽衍免喪後。其親盡神主。將遞遷于先生宅。以長房也。先生將秖迎于中路。着黑笠。衣布道袍服帶。出門外數馬場。諸行當到。先生小止。轝者伏地再拜。因隨行從者請乘轎。先生不許。至家行祭。更無告辭了後。巾服乃復如初。
先生遭服。常着布巾。遂發頭風。至於喎斜。更着布梁冠。
正月以來。倭擾汹汹。先生雖在憂慽之中。不勝憤惋。逢人輒語到。辭色必勃如也。一日座首李一煥來謁。先生又問時耗如何。李答。近聞倭下陸已多日。自廟堂和論流行。而但順適其意。日日饋餉。至於以我人爲倭供薪水之役。聞之不覺氣塞。先生曰。今日始聞快心語也。人不當若是耶。蓋傷恬戲日久。賊情方叵測。人無敵慨之義。而晏然如處堂之燕雀也。
先生曰。中國人素該音律。故出言屬文。文從字順。無不諧音。所以詩文雖得刱出。亦皆合律。東人不解音律。故但效華人文字耳。
先生曰。人必多與於人。方是做好人。於德操文饒。跡其數件事。則餘可類推。若不如此。豈足爲二人。
司馬徽德操。襄陽人。嘗有人亡猪。妄認徽猪便推之。後得亡猪。以猪還。因叩頭自責。徽厚致謝。劉寬文饒。弘農人。嘗行。有失牛者。乃就車中認之。寬無所言。解與之。下車步歸。有項。認者得牛還。叩頭謝曰。慚負長者。隨所刑。劉曰。物有相似。事容脫誤。幸勞見歸。何爲謝之。
先生命其孫宇蒙曰。拜始於鞠躬。非始於跪膝。故肅拜與公拜。唱笏鞠躬拜興平身云。今人拜時。先跪膝後拜首。殊失拜儀。仍起躬拜示之。且敎曰。拜時爲先鞠躬義手。却先據地。脚不要跪而自跪。且拜不容不速。不可緩慢也。
先生喟然發嘆曰。善乎任丈之觀化也。余對任丈之春秋。尙未洽七旬。而且其家事聊落。豈曰善乎。先生曰。自今以後。喜怒哀樂都不知。寒暑飢飽亦相忘。豈不善乎。坡詩云。大患由有身。古詩云。蓋棺事已定。蓋棺已前。百事終未定貼。而以後方見都無一事。
先生曰。趙重峯家貧好讀。牽犢而牧。必抱書隨讀。親堂然柴。亦照而讀。若是則貧如人何。且曰。自古賢儒。稟得一種別性。重峯幼時與兒輩。戽野水將捉魚。水未涸日已暮。諸兒皆散歸。獨重峯涸水得魚。此在通津時事。後居湖中。出入必載松明而行。止宿處輒燃而讀書。一日夜逢一人語曰。子見擊蒙要訣乎。曰。未也。曰。爲士者。可不知乎。卽夜燒松。書而與之。以凡人之性。豈如是乎。
先生曰。商辛以天子爲象箸。箕子嘆曰。稱此以求。雖天下不足。漢文帝欲起臺。謀諸工。工曰。可費百金。帝曰。百金。中人十家之産。遂罷之。又聚上書囊以爲帷。曹操雖小兒斥以巧詐多謀。而及其卒也。史述其行曰。軍勞宜賞。千金不惜。無功妄施。一毫不與。宋仁宗夜思燒羊。欲求之。復止之曰。如是則天下受其害者必多。此皆帝王家謹財用。猶如此。楊萬里之子長孺。號東山。爲河南刺史。仇泰然爲四明太守。泰然才識了了。每與欣接。一日泰然言家用不贍。東山怪然曰。方爲外任。何用不贍。泰然曰。食口四十餘。每日晩飯具小肉。夕不具肉。猶爲不足。東山曰。我爲刺史。有不能食肉。子爲太守。猶食肉耶。遂疏泰然。今之人無捧祿。而或有殺牛置酒。無事燕樂。可惜。
先生曰。人若要快心。後必有殃。且曰。昔郭子儀威權莫比。時盜發子儀父塚。捕之不獲。人以魚朝恩素惡子儀。疑其使之。子儀入朝。朝廷憂其爲變。及見上。上語及之。子儀流涕曰。臣久將兵。不能禁暴。軍士多發人塚。今日及此。乃天譴。非人事也。朝廷乃安。亦有爲而發也。
丙子十二月五日曉。先生曰。起起士弘乎。夜夢作歌三闋。只記得首句曰。功名도너ᄒᆞ여라。豪傑도나스르여。語短意長。天然成章。無乃吾命辭歟。對曰。此闋深寓避世之意。乃先生志事也。因請足成。先生曰。恐製作之不似天然耳。俄而續之曰。門다드니深山이오。冊펴니師友로다。오라난ᄃᆡ업건마난。興다ᄒᆞ면갈가ᄒᆞ노라。【已上二十三條。記先生雅言及庸行。】問今云壬辰後。始有倭關是否。先生曰。壬辰前已有之。蓋兩國關市處也。今雖朝籍之士。或不免於云云。一笑。又問俗行壬辰錄。多有不經之說。似是好事者爲之。先生曰。若據此而爲言。則烏得免無識也。因言日本大姓膝橘源平。所以關伯不出此四姓。秀吉非平氏。而因冒托爲關伯。又所謂小西飛。卽姓小西。而守飛彈也。故謂之小西飛彈守。而俗訛如是。又有要時羅者。倭國諜使也。今云要時郞者。亦俗訛也。
問大練之練。先生曰。麤帛也。因問於何見之。曰。於馬后事見之。又曰。此后甚賢。明太祖后馬氏亦賢。奇事。
問我國有關王廟。未知何也。先生曰。關王。中國人皆尊崇之。至有疾病亦禱之。海商船入。抱塑像而行。故天將始出我國。立廟於京城東門外。劉綎於南原立之。陳璘於水營立之。蓋欲祈福勝戰也。
問今人有役鬼之說。往往有學之者。似甚無據。先生曰。此或有之。康節云。鬼之畏人。有甚於人之畏鬼。凡人爲善。則陽日盛而鬼畏之。爲惡。則陰日盛而鬼狎之。詩云。神之格思。不可度思。矧可斁思。殷人尙鬼。皆敬畏鬼神。今人不知有鬼神。若使知有鬼神。則必不甚作惡。
問沙麓。先生曰。春秋書沙麓崩。以爲災異。漢孝元皇后王氏。生沙麓之下。漢儒以爲沙麓之崩。應今日沙麓之慶。
問或云朱夫子九遷其墓。是否。先生曰。否。恐至三矣。
問京在所。先生曰。古有其制。如今留鄕也。蓋以朝官中姓貫於此鄕者爲之。如安東京在。則安東金氏。爲之類也。
問古有戊巳校尉。戊巳何意歟。先生曰。干支各有定位。而唯戊巳則無矣。校尉亦有定數。而此校尉在定數之外。若方位之戊巳歟。
問近來人家有神主繼后。何如。先生曰。子不看買土買婢乎。新主舊主對坐。與之受之而後可也。繼后何等重事。而以黃泉冥漠之魂爲之乎。與之者誰。受之者誰。古有冥婚。何異於是。
問性情意義。先生曰。性字看其爲字。則可知也。從心從生。是心之生理也。余曰。性之爲生理。旣聞命矣。情字從心從靑。豈非生理之發者爲苗之靑者乎。先生哂之。
問今俗於昏家稱査。或稱記下。未知如何。先生曰。査字無出處。乃俗稱也。記下之稱。似無不可。又曰。梅山丈於其繼母之父。稱侍生云。余對爲汲也妻者。爲白也母。則雖繼母之父。直稱侍生。似涉未安。先生曰。直敎嘗以此問余。答何叔京非鄧氏外孫。而稱鄧舅。則以此推之。似不可以侍生自稱。且服制與稱號。亦相不同。旣爲其母之黨。則不爲繼母之黨矣。又問爲其繼外祖者。亦當何稱。曰。以尊侍禮處之。不可以外祖自處也。
問幼而不能服其母之黨。長而遭繼外黨之服。服之否。先生曰。雖外黨。禮無二統。幼而未服。與服何異。
問婦人不得已主祭。則改題當如何。先生曰。夫之祖父曰大舅。曾祖曰曾大舅。高祖曰大曾大舅。因曰。妻之祖父。稱外大舅。自稱彌甥。
問孟子曰。乃若其情。則可以爲善也。又曰。若夫爲不善。非才之罪也。不言性。而言情與才。何也。先生曰。性者無形可據。故言情與才。以其形著而然也。
問井田畝。先生曰。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。百畝則長廣皆百步。以今較之。似優數石地。
問延年仕宋。恐非淸流。淵明友之。何歟。先生哂曰。此事甚難。在晉名士頗多。惟不仕。稽康阮籍若箇人而已。
問駔僧俗音低快。何如。先生曰。古音長灰。當以古音爲正。因敎凡字之音。多不可從偏傍解之。詩不云乎。以薅荼蓼薅音好。心嘗疑之。近按說文。薅字從女。是好者省。故音好。可呵。
問書多方。陳新安疏所謂成王政序。多方序何在。先生曰。成王政。是逸書也。無其書。而篇名則傳之。序卽小序也。朱子已刪定。故今不載見耳。
問有族人身死無子。只有老母寡妻。議立后而無許入者。取降族家兒繼之。今年將冠。諸議以爲不可升孼爲嫡。固知此議之無據。而喩之莫曉。奈何。先生答。其云不可者。使無所歸之窮人。必絶其香火然後。快於其心乎。
問書云。天惟時求民主。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。刑殄有夏。又曰。非天庸釋有夏。非天庸釋有殷。又曰。天惟式敎我用休。簡畀殷命。天旣降休于成湯。殄滅有夏。則恐不可謂非天庸釋有夏。式敎周王。畀付殷命。則亦不可謂非天庸釋有殷。但天道爲福善禍淫之理。而惟在自取之如何。且庸字有心之謂。則非天偏有心之謂歟。先生答。此說然。
問喪禮云。姑母之子曰外從。表叔之子曰內從。此從內外親之屬之意。而俗則反是。先生答。俗稱果相反。
問母之兄弟曰內舅。亦內親之屬而謂歟。表內之意相反而同稱。未解。先生答。對父族而言。則凡異姓皆外也。而異姓又自有內外。
問妻之父曰外舅。自稱曰外甥。外字初無親屬之分。而以其相外之義而稱歟。舅甥之說。亦無所據。而或云朱文公與蔡沈。以舅甥而爲翁壻故云是否。先生答。外字所以別於內舅。或說非也。
問逸民不言泰伯大連。小大連先小後大。何也。先生答。泰伯之不言於逸民。泰伯君於句吳。不可謂逸民。不言大連。未詳。小大先後。或有俗說。而不見的據。
問詩鳥覆翼之覆字反切。與今行諺解不同。先生答。反切甚當。諺解之音不可曉。叶音乃古韻。今音不用。
問易三十六宮。先生答。三十六宮之說。有數般。而其不易反易之說。最明白。蓋六十四卦。不易者乾坤坎離中孚頤大小過八卦。其外五十六卦。乃二十八卦之反易也。合不易八。爲三十六。六十四卦。其實三十六宮而已。
問周尺著於圖式者。長短不齊。當誰適從。先生答。此非攷定鍾律。則長短不必深計。但以廟中前代神主爲準。使無長短不齊之患則可矣。
問內艱陷中不書貫鄕。而今多書之。有第幾而今則不書。先生答。陷中貫鄕。俗禮之無妨者也。第幾。其族中行第。今俗所無。不必論。【已上二十八條。記問答】
奇慶衍知其安穩平淡。又有志於學勤篤甚。先生每稱之。及丁憂。不食肉醯。與人言。未嘗見齒。其天性篤至。豈易得哉。時年二十六。眞畏友也。
同副承旨崔益鉉上疏略曰。三公六卿無建白之議。臺諫侍從避好事之謗。朝廷之上。俗論恣行而正議消。諂佞肆志而直士藏。彛倫斁喪。士氣沮敗。賦斂不息。生民魚肉。以致天災見於上。地變作於下云云。聖批優容。至有戶參除授之命。以彛倫斁喪四字。大臣聯箚。三司交章。泮儒捲堂以至前啣散官。攻崔日急。竝皆嚴譴斥罷。玉堂權鼎鎬於經筵奏對之際。極口巧辭。百道攻崔。小人陷人之情狀。醞釀平日者。綻露無餘。聖敎有曰。漢之汲黯。至有陛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之語。今此崔疏。有何過重哉。毒藥苦口利於病。忠言逆耳利於行。若鞫如此忠直之人。則載之史冊。天下後世。謂我何如主耶。司諫吳慶履。修撰權益洙。上疏言事。末攻權鼎鎬。上嘉納焉。權鼎鎬卽命刊削。時論快之。
戶參崔益鉉又辭疏。尾伸前疏未盡之意。凡六條。復廟設院罷胡錢息賦斂禁鬼神出後追律國賊。辭甚切直。不避時諱。疏將上。告其父。父曰。自爾登第之日。委身於君。事君盡忠。更復何言。乃謂其子曰。吾呈此疏。首領難保。語到身後事。其妻曰。丈夫爲國盡忠。死猶榮焉。更有何瑣瑣身後語效兒女之爲也。乃決意呈疏。待罪樓院。疏上有多有語逼之批。攻箚劾章。急於向時。不得已有拿鞫竄配之命。就鞫上使武臺監視。蓋慮其有酷刑也。纔施刑。卽命撤鞫。方其囚禁府也。其子待罪門外。日寒甚。廛人各以裀席覆籍防風。又買溫湯饋之。相續於道。及其發配也。餞迎擁路。自是言事。投疏相繼而起。崔實倡之也。
掌令洪時衡。繼崔上疏。切中時弊。上嘉納。卽除修撰。有一臺諫構誣疏。沮以爲洪宰康津時。父死不發喪。幾日磨勘云。蓋應署吏詬罵之說也。洪時衡之父。死於康津。洪以箋文使赴京。返至公州聞喪。噫。古有讒第五倫笞其婦翁者。何代無賢。
司直洪萬燮上疏。以爲崔益鉉其家傔之外戚。家世寒微。而揚揚於士大夫之列。噫。崔乃孤雲之後。文獻可徵。而構誣如是乎。設是寒微。寒微者不得正言直諫乎。渠以不寒微而所言乃如是乎。曾有權貴者之妾。祈子于名山。而洪隨跟而至。遙立十步許。彼一拜。已亦一拜。祝曰。願使此夫人生好男子云。竟取富貴。其汚行素如此。聖敎與奇趙竝稱。不可以人類責之者。可見魑魅鬼蜮無所逃於白日之下也。趙愿祖竝攻崔洪。辭甚醜陋。槪與萬燮一口也。會一進士。今番慶科東堂將左赴束裝矣。左試官韓章錫。歷謁先生。會一謂有隨行之嫌。更赴右策土場由。府內人張文逸請小間。會一曰。有所欲言則言之。何必屛人。張曰。今幕裨聞執事綴策如流。願一見之。而不能造館者。恐礙人耳目。請屈營下不敢望也。所以坐鄙舍要見之以僕紹之云。會一遜辭謝之。張固勸之。會一曰。吾無片技寸長。誤承垂勤。愧恧不勝。且以應試之士。往見幕裨。恐非體面。善爲我謝之。竟落山外人或惜其未參。余曰否否。會一之此一事。足以激厲一世。以正士習。其得失豈足欣戚哉。顧此世降。士習浮薄。狗苟而蠅營。得之則喜。非但自喜之也。相知者亦爲之喜。不得則憂。非但自憂之也。相知者亦爲之憂。擧世滔滔。莫知爲非。哀哉。
奇正言陽衍。出仕路而不失讀書時氣像。余甚敬之。
南坡李丈。年洽八耋。嗜書如土炭。對冊必整冠端坐。不以老少懈讀了。亦必奉于尊閣。正其部帙。不使亂錯。嘗曰。夫聖賢之書。其可慢忽乎。其抱負甚博。先生每許之。【已上八條。記藏否得失。】